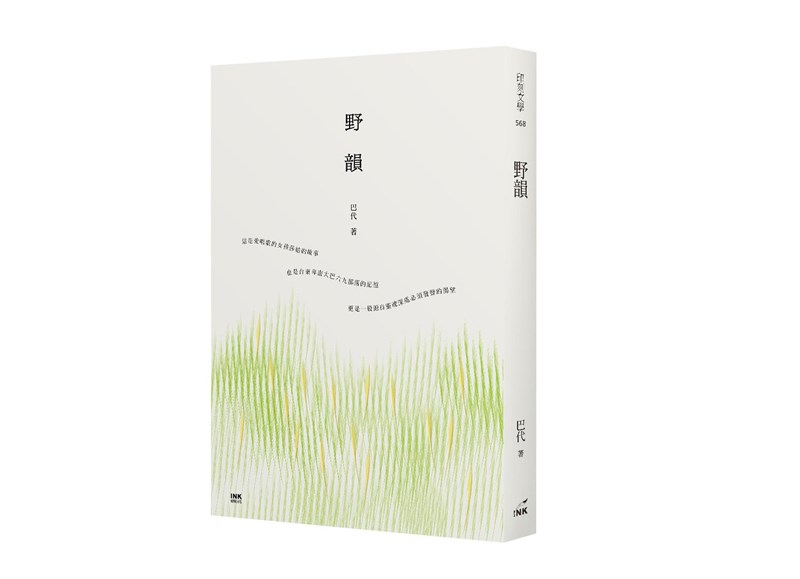 《野韻》
巴代是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裔,專職寫作的他曾獲山海文學獎、金鼎獎最佳著作人獎、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吳三連獎、全球星雲文學歷史小說獎。這本《野韻》正是巴代內心靈魂對部落情感歸依之作,如鮭魚逆溯溪流尋找生命的源頭。
圖/印刻提供
《野韻》
巴代是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裔,專職寫作的他曾獲山海文學獎、金鼎獎最佳著作人獎、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吳三連獎、全球星雲文學歷史小說獎。這本《野韻》正是巴代內心靈魂對部落情感歸依之作,如鮭魚逆溯溪流尋找生命的源頭。
圖/印刻提供
文/陳秋萍
巴代是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裔,而這本《野韻》也正是巴代內心靈魂對部落情感歸依之作,如鮭魚逆溯溪流尋找生命的源頭。
誠如巴代在這本書的〈後記〉寫道:「我寫《野韻》,也是我對部落文史工作的調查、記錄與整理之後,一種文化的警惕與焦慮。部落,會不會如小溪那般,在大社會主旋律之外,即便鮮明的擁有自己的記憶、節奏、旋律、音韻與情感,也迴避不了外部因素的強烈主導與干擾。部落的未來,終究只是瘖啞、無語?或者慘落到悲鳴甚至消失而『無鳴』?最後,只能成為別人的記憶與紀錄?」
巴代筆下的卑南女孩莎姑,出生台東大巴六九部落,正值台灣日據時期。從小就被父親送養給姑姑與日本姑父,當姑父揹著她離開家時才三歲,但莎姑隱隱約約地觀察周遭環境並記得經過一條溪流,自這條溪流過後她的人生也自此轉變。
摸索回到原生家庭
莎姑並不受養母喜愛,甚至常遭受虐打,幸好養父松本待她如同親生女兒呵護,莎姑才有比較快樂的時光。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戰敗,養父早逝,只好跟著養母來到關山生活,期間生活依舊孤苦無依,不僅要打理家務,養母三不五時便找莎姑麻煩,生活的窮困與精神上的孤單,令莎姑決定逃離養母身邊,憑著當初養父背著她離家時的記憶,循著模糊的路與印象深刻的小溪終於回到原生家庭。
回到家的莎姑內心無比歡欣,母親更是驚喜萬分,羞愧自己沒能保護女兒,唯獨父親絲毫不受影響,更不覺得自己把女兒送給別人有什麼好罪惡的,莎姑原以為的父愛終究只停留在養父松本的回憶。沒想到親生父親時常喝得爛醉,全家人都怕父親,只要他一發酒瘋母親便趕緊帶著兒女逃到山裡躲著,一夜未歸更是常景。
母親的懦弱,弟妹的年幼,激起了莎姑一肩擔起家務的重責。面對父親不負責的任態度與無數次的酒瘋暴打,莎姑勇敢的反抗;另一方面也開始為自己的將來打算,決意與愛慕自己的德里結為夫妻,自組家庭。由於自小無法從原生家庭得到滿足的愛護,莎姑非常重視家人,再窮困都堅決不送養孩子,與丈夫一路扶持。
繼續唱著生命之歌
莎姑自小命運坎坷,將近六十歲了也沒有所謂的大富大貴,但是莎姑知足,將孩子扶養長大各個平安孝順,有了家是她最大的安慰。而丈夫雖然罹癌,也不怨天尤人,努力復健。除了家庭,另外支持著他們的是堅定的信仰。由於生活周遭時常見到各類宗教信徒,發現不管是什麼宗教信仰總是教人的心靈充滿能量,靈魂彷彿也有一個家。於是,他們重新找回天主找回祖靈,不僅如此,他們也希望團結部落的族人一起將因為被殖民關係而失落的傳統文化興盛起來。
愛唱歌的莎姑自然擔起傳統歌謠傳唱的責任,她的歌聲情感飽滿,常使族人聽得忘我,或許是因為在莎姑的生命河流中,遇過太多的溪石衝擊著,她明白生活的箇中滋味,一路走來有磨難也有愛與希望,所以莎姑唱起歌來情感特別豐富動人。部落也因為受到他們夫妻的影響,共同將部落的祭典一一舉辦,更是讓年輕人了解自己的文化底蘊,信仰使得他們生活的無憾踏實。
丈夫終究敵不過病魔離世,莎姑再度面臨生離死別的悲傷,儘管如此,她仍然如常的生活,繼續地唱著生命之歌,猶如她記憶的小溪,不停的奔流,流向大海流向愛的歸處。
巴代是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裔,專職寫作的他曾獲山海文學獎、金鼎獎最佳著作人獎、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吳三連獎、全球星雲文學歷史小說獎。這本《野韻》正是巴代內心靈魂對部落情感歸依之作,如鮭魚逆溯溪流尋找生命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