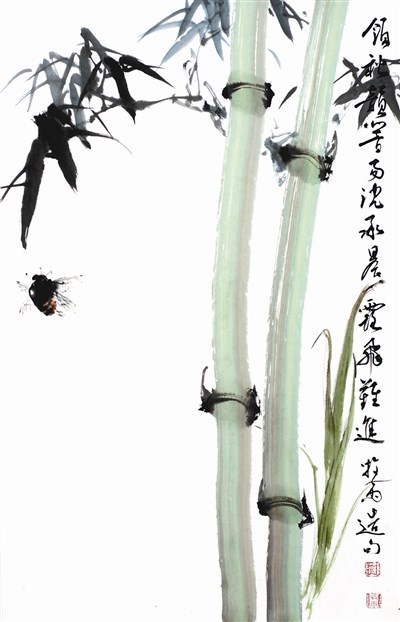
每到炎炎夏日,蟬聲響徹整個山林。據說蟬為了鳴噪這一季,必須在地底蟄伏十幾年。這付出與獲得,是否成正比,可就見仁見智了!
另有說蟬分為兩種,春季生夏季死謂之「夏蟬」;夏季生秋季死謂之「秋蟬」。所以莊子在〈逍遙遊〉裡說「蟪蛄不知春秋」,這「蟪蛄」就是蟬的別稱。不過莊子這句話並不單純只是說明蟬的自然生態,而是以蟬喻生命短暫而局限了牠們的見識,所謂「秋蟬不知春,夏蟬不知秋」,就用來諷刺一個人的見識淺短。
到了唐代,詩人們就不以這樣來說蟬了。虞世南有這樣的〈詠蟬〉詩:「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借秋風。」
「飲清露」,是歌頌蟬吃的東西非常潔淨;「出疏桐」,說明蟬住的地方是與鳳凰一樣高雅的梧桐;而蟬聲之所以能傳得遙遠,是因為居住在高處,而不是依託秋風而遠颺。
蟬是這樣,人應該也是這樣,聲名能夠遠播,必是品行高潔,而不是依附別人聲望的緣故。從此,這「高潔」,就成了蟬的代名詞。
唐高宗儀鳳三年(六七八),駱賓王任侍御史,因上疏論事觸忤武后,遭誣,以貪贓罪名下獄。他寫了一首〈在獄詠蟬〉,來表明自己的高潔與無奈:「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餘心。」
這時已不是歌頌「垂緌飲清露」,而是慨嘆「露重飛難進」;也不是讚賞「居高聲自遠」,而是感喟「風多響易沉」的無奈!沒有人相信我的高潔,除了藉助蟬,還有誰能表達我高潔的心意呢?
同樣蟬的身影,詩人在不同的心境之下,竟然產生如此巨大強烈的對比。我們不得不佩服他們豐富的想像能力。
到了李商隱,蟬又被一轉折,成了「清貧」的代名詞:「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這時同樣的居高飲露,卻被詩人形容成餐風飲露難以飽腹。所以不管如何哀鳴,都是徒勞費聲。縱使叫到精疲力絕,聲音變得稀稀疏疏、斷斷續續,這一片梧桐仍然無情的兀自碧綠。
自己當個小官到處漂泊,家園也都已荒蕪零落。這時突然想到:原來蟬常常以鳴聲提醒我,我們同樣都是舉家清貧的啊!這樣的蟬聲,聽起來實在讓人不勝唏噓。
然而,還有更甚者,根據馬縞《中華古今注》:「昔齊后忿而死,屍變為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為齊女焉。」
蟬成了含怨齊女的魂魄,一季蟬鳴,斷斷續續、哀哀婉婉,是向世人呼喊冤屈的淒唳!
蟬短暫的生命,與拚命的呼啼,在詩人的靈魂深處,自然挑起了悲劇的情懷。甚至文人用以自許的「高潔」,自古以來,原本也是不太能見容於這個世俗的世界,「飲露身輕、吟風翅薄」,就是這樣的結果。
所以學學王維吧!潔身自好之外,也必須具有豁達的心胸,否則易淪於自怨自哀的情境。
王維的「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只是在告訴友人他在輞川的生活,是何等悠閒、何等自在。王維〈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
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
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