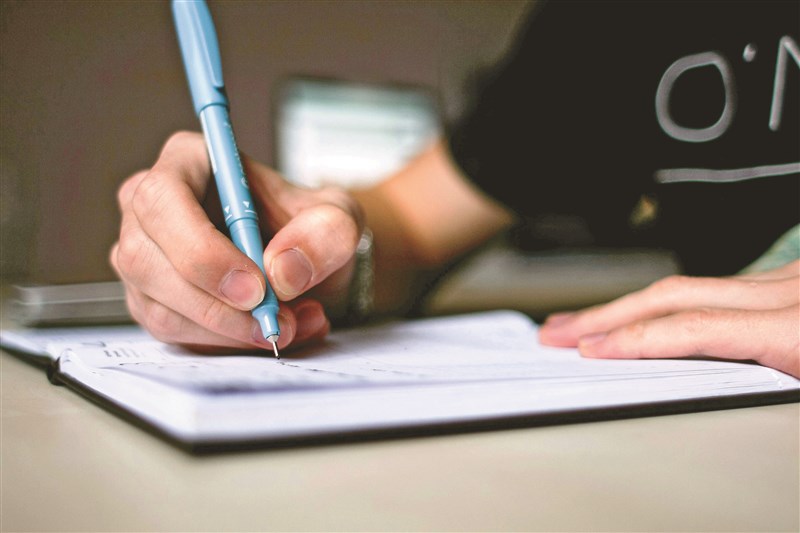 撰寫故事時,可往人性需求,一層層挖下去。圖/Pexels
撰寫故事時,可往人性需求,一層層挖下去。圖/Pexel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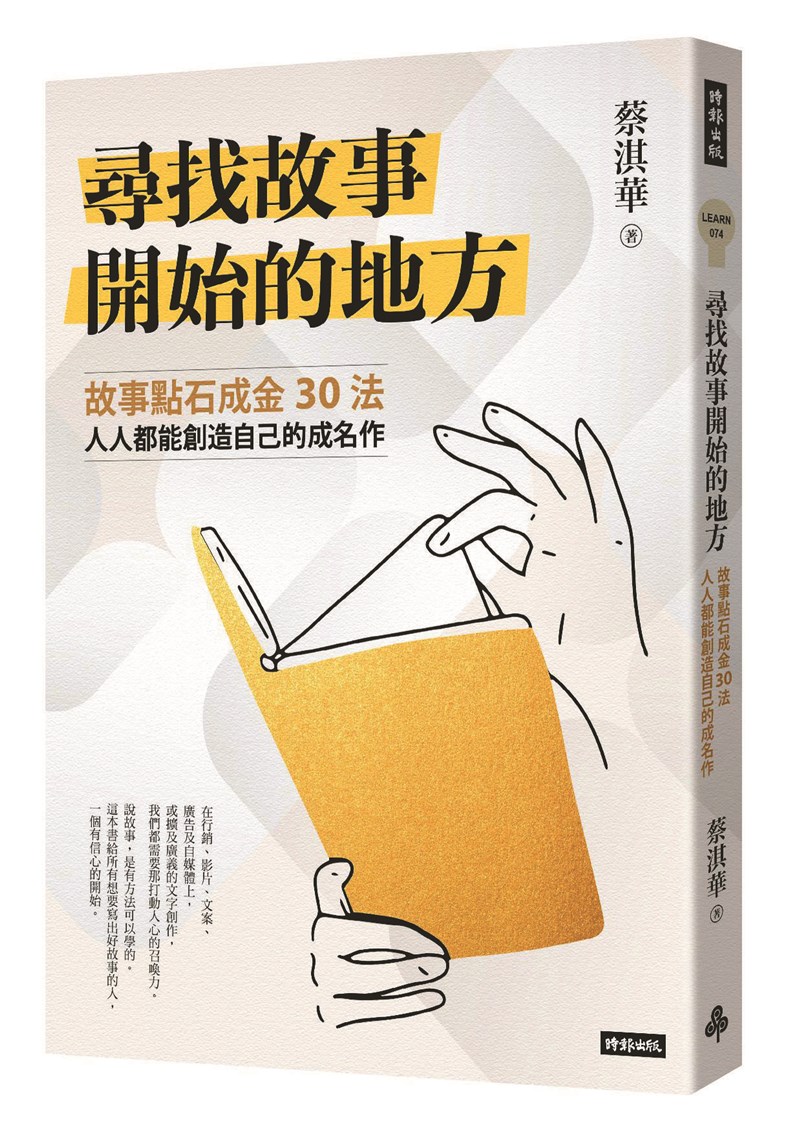 圖/Pexels
圖/Pexels
文/蔡淇華
一樣是鋼彈類型片,筆者看完《變形金剛》,走出戲院時,感覺到空洞悵然。但看完《鋼鐵擂台》,卻覺得一顆心滿滿的。思考觀影經驗的殊異,發覺不在於製作成本高低,而在於劇本主題層次的經營。
藝術好壞的評斷標準,是「有意思」,也就是不能停留在表層,要有「第二層」的意思。
《變形金剛》的故事「失之太直」,只停留在絢麗的打鬥。然而《鋼鐵擂台》的編劇卻願意在老哏中玩出新意,用心走向更深層的人性。《鋼鐵擂台》劇末,機器人亞當的聲控裝置被對手擊毀,兒子只好將亞當切換至視覺模仿模式,並要父親在場邊揮拳,讓亞當模仿,最後竟然逐漸扭轉頹勢。這一幕設計很少被影評人提起,然而卻完全點明親子教養的真諦:教養孩子,不能只用嘴巴,要用行動做給孩子看。因為教育之道無他,愛與榜樣而已。是這樣精準的故事設計,讓《鋼鐵擂台》比《變形金剛》的藝術高度,更上了一層。
德國作家雷馬克(Erich Paul Remark)於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小說《西線無戰事》,故事結束在男主角死於狙擊。「一九一八年十月,他陣亡了,那一天,整個前線是那麼沉寂和那麼寧靜,戰報上僅僅用一句話來概括:西線無戰事。他是往前面仆倒下去的,躺在地上,好像睡著了一般。把他翻過來,人們看得出來他受的痛苦並不長;他臉上的表情很安詳,差不多像是滿足的樣子,高興結局已經來臨了。」
無戰事、安詳、滿足、高興,是字面表層,卻更深刻反諷「西線有戰事」,以抗議一戰時,德軍大量的傷亡。這部小說反戰的「第二層涵義」太明顯了,難怪於一九三○年代被納粹德國查禁。然而好的藝術是永恆的,《西線無戰事》二○二二年被重新拍攝,代表德國角逐第九十五屆奧斯卡金像獎,最終獲頒最佳國際影片。
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於一九八四年所寫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男主角只想追求輕盈沒有責任的愛情,然而卻發現那種輕盈,允許女主角去尋找其他伴侶,卻會帶給心靈無法承受的沉重。所以這本小說真正想探討的,是與書名相反的「第二層涵義」: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是這樣的在愛情沉重的負擔與燦爛的輕盈間,做反覆的辯證,顯現出生命多層次的樣貌。
動機也有層次
故事是「動機」加「行動」的輪迴,動機是鼓動故事不斷前進的主要力量。例如觀看《阿甘正傳》,看不懂的人,只會對無厘頭的情節莞爾一笑,以為阿甘忽然跑出宅邸,並且欲罷不能橫越美國,一跑三年。當人們問他為何而跑,他只回答沒有原因,其實不然。阿甘生存的最大動機,是「歸屬感和愛」。
如同馬斯洛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生理」、「安全」、「歸屬感和愛」、「尊重」、「自我實現」。「生理」與「安全」需求對阿甘而言,根本不放在眼裡,他可以不要命的一再衝回叢林裡救人,也可以致富後將財產都送人,如他說的:「一個人真正需要的財富就那麼一點點,其餘的,都是用來炫耀。」他智商不高,但他很清楚說出:「我不是一個聰明的人,可是我知道什麼是愛。」
失聯多時的珍妮主動來找阿甘,吐露愛意,溫存一夜後,竟在隔日清晨不告而別。茫然不解的阿甘,才會因為珍妮跑起來。因為最初是珍妮叫他快跑,躲避霸凌,所以跑步成了他人生遇到困難時的最好解藥。當阿甘失魂落魄時,他思念珍妮的方式,就是跑步。《阿甘正傳》推動情節的內在動機,是「愛」。
又如《金法尤物》上演至今二十年,仍然成為許多影迷的心中經典,是因為女主角一開始是個樣板的「金髮美女」,為了「搶回男朋友」的「外在動機」而去念哈佛。但最後卻從「捍衛女權」,得到「自我實現」的「內在動機」,因而找到讀書的樂趣,最後甩掉智識不如他的前男友,以榮譽生畢業。
事實上,不管是娛樂片或是藝術片,幾乎都可以在主題層次的深化中,讓主角找到更深層的「內在動機」,因而成就偉大的故事。以後觀影時,讀者不妨思考主角行為動機的轉變;甚至在撰寫小說或劇本時,除了寫表層的故事,也別忘了往人性的需求,一層一層的挖下去。(摘自《尋找故事開始的地方:故事點石成金30法,人人都能創造自己的成名作》,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蔡淇華
1966年生,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畢業。現任台中市立惠文高中教師兼圖書館主任。曾獲台中市文學獎首獎、新北市文學獎首獎、台中市詩人節新詩創作首獎、總統教育獎主題曲首獎、教育部師鐸獎、星雲教育獎。
出版著作:《青春微素養:36個通往更理想自己的基本功》、《寫作吧!一篇文章的生成》、《青春正效應:新世代應該知道的人生微哲學》、《寫給年輕:野百合父親寫給太陽花女兒的40封信》、《寫作吧!你值得被看見》、《寫作吧!破解創作天才的心智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