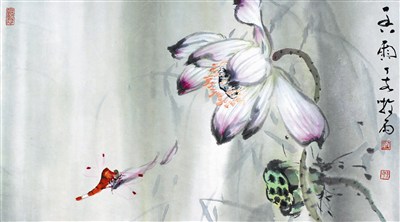
荷花入中國古詩甚早,在屈原的離騷就有這樣的句子:「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這裡所說的「芰荷」以及「芙蓉」都是荷花的別名。宋朝姜白石詠荷名句:「水佩風裳無數」的概念,想必源自於此。以荷葉為衣、以荷花為裳,或說荷花是水的佩飾、風的衣裳,真是浪漫至極。
白石此句出自〈念奴嬌〉一詞。根據其序文的說法,白石有一段時間客居武陵,在這個古城野水之地,喬木參天,跟著兩三個好友蕩舟其間,大夥兒緊挨著漂亮的荷花飲酒作樂。而且因為已是秋天,有些地方水澤乾涸,荷葉從地面往上竄出,有一丈之高。
大家列坐其下,頭上被密密麻麻的荷葉蓋住,幾乎不見天日。
這時,每有清風徐徐吹來,就感覺到許多綠色的雲彩在空中飄動。偶爾,在荷葉稍稍稀疏的地方,會窺見乘坐畫船前來賞花的遊客,這種意境,實在美妙動人!
後來白石離開武陵來到杭州,又有數次機會,與好友夜泛西湖,倘佯在荷花之中,這種光景,堪稱人間奇絕!
詞人與芰荷的兩次邂逅,讓詞人不禁詞興大發,寫下了這闋千古絕唱的詠荷名詞:
鬧紅一舸,記來時嘗與鴛鴦為侶。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風裳無數。翠葉吹涼,玉容銷酒,更灑菰蒲雨。嫣然搖動,冷香飛上詩句。
日暮青蓋亭亭,情人不見,爭忍淩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風南浦。高柳垂陰,老魚吹浪,留我花間住。田田多少,幾回沙際歸路。
字字珠璣、句句精采。把荷花的「情」、「意」、「境」推到了極致。
原來,在文學長河裡,讓我們對藕花永遠吟詠不已的,正是這嫣然搖動而飛入詩句的冷香啊!
荷花如此的出塵與清麗,每每讓歷代詩人無法忘懷,因而寫出許多膾炙人口的詩句。
譬如,唐朝詩人白居易,在他的〈長恨歌〉裡,就用「芙蓉」來形容楊貴妃嬌嫩的臉龐:「……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原來讓唐明皇每每流淚的,竟是未央宮的芙蓉與柳枝,因為芙蓉的嬌嫩與柳葉的清秀,總不能不讓君王想起那「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玉環!
而宋朝女詞人李清照亦有佳作:
〈如夢令〉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
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
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畢竟男女在個性上是有些差別的。白石直入藕花身處,到三十六陂人未到之處飲酒作樂;而我們的女詞人,卻是因為沉醉於花的美麗,而至「不知歸路」,直到「興盡晚回舟」,然後才「誤入藕花深處」,結果「驚起一灘鷗鷺」。
這「驚起」強化了「誤入」,「誤入」強化了「沉醉」,而「沉醉」又強化了藕花的迷人。幾個句子,就這樣來回相互激盪,最後,盪出了整闋詞的動人意境與醉人的特質。
雖然歷代的詠荷詩詞甚多,但大都不離浪漫花間,或擬花為美人一派。唯有周敦頤的〈愛蓮說〉,將荷花從感性唯美的雲端,拉到理性道德的範疇。
〈愛蓮說〉裡,有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句,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最後還封蓮為「花中君子」,從此荷花在「蓮花」、「菡萏」、「芙蓉」、「芙渠」、「藕花」等眾多別稱之外,又多了一個「君子花」的稱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