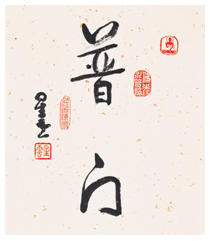
曾有許多人問我:「為什麼佛光山有這麼多的佛教事業,都是以『普門』為名?」這句話往往將我的思緒帶回五十多年以前……
一九四九年,我初來台灣時,曾經度過一段三餐不繼,顛沛流離的日子。記得在南昌路某寺,曾被一位長老責問:「你有什麼資格跑來台灣?」到了中正路某寺掛單,也遭拒絕。因夜幕低垂,我只有緊緊裹著被雨水淋濕的衣服,在大鐘下躲雨露宿。第二天中午時分,在善導寺齋堂裡,看見一張八人座的圓形飯桌,圍坐了十五、六個人,我只有知趣地默然離去。
在走投無路下,我想到或許可以到基隆某寺去找我過去的同學,當我拖著疲憊冰冷的身軀,冒著寒風細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達山門時,已是下午一點多鐘。寺裡的同學聽說我粒米未進,已達一天之久,趕緊請我去廚房吃飯,可是就在這時,旁邊另外一個同道說話了:「某法師交待:我們自身難保,還是請他另外設法好了!」
當我正想離開之際,同學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錢出來買了兩斤米,煮了一鍋稀飯給我吃,記得當時捧著飯碗的雙手已經餓得不停顫抖。向同學道謝以後,在凄風苦雨中,我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於這段刻骨銘心的經驗,我當時立下誓願:日後我一定要「普門大開,廣接來者。」二十年以後,我實現了願望,先後在台北成立「普門精舍」、「普門寺」,教導所有的徒眾都必須善待信徒香客,讓大家滿載歡喜而歸。直到現在,佛光山的各個別分院仍然保持一項不成文的規定:每一餐多設兩桌流水席,方便來者用齋,對於前來掛單的出家人,則一律供養五百元車資。此外,我又在佛光山開辦中學、幼稚園,乃至佛教雜志,都是以「普門」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門示現」的意義,希望徒眾都能效法「普門大士」的精神,接引廣大的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