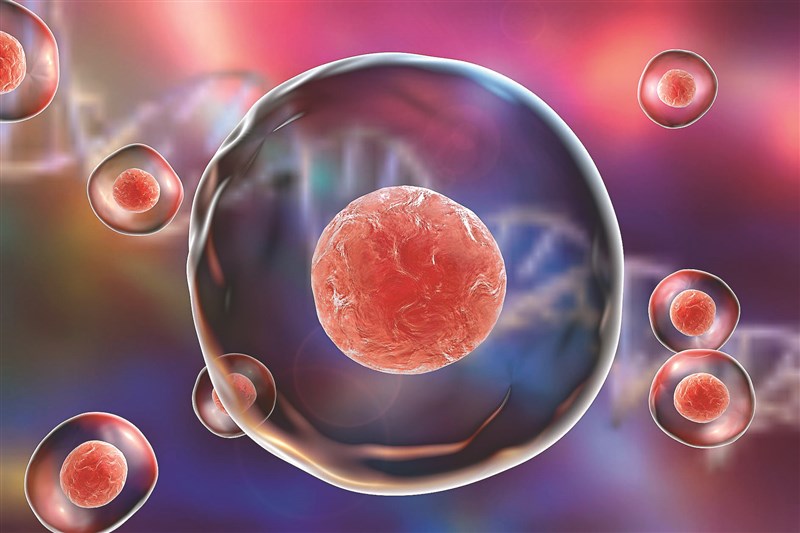 能夠使血液恢復活力的細胞被稱為「造血細胞」,或「幹細胞和祖細胞」。圖/123RF
能夠使血液恢復活力的細胞被稱為「造血細胞」,或「幹細胞和祖細胞」。圖/123RF 人類的「回春」指的是細胞不斷的補充,通常來自幹細胞或祖細胞庫,以因應細胞的自然死亡和分解。圖/123RF
人類的「回春」指的是細胞不斷的補充,通常來自幹細胞或祖細胞庫,以因應細胞的自然死亡和分解。圖/123RF 家母腳踝骨折,傷口雖然恢復甚慢,但仍然癒合了,可是她的膝關節腫脹卻無法逆轉。(示意圖)圖/123RF
家母腳踝骨折,傷口雖然恢復甚慢,但仍然癒合了,可是她的膝關節腫脹卻無法逆轉。(示意圖)圖/123RF
文/辛達塔.穆克吉(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癌症醫師)
「老年是一場屠殺」,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寫道。但其實它是逐步衰弱──一個傷害又一個傷害的持續碾磨,阻擋不了的功能衰退終致功能障礙,以及無可避免的喪失復原的能力。
人類藉由兩個重疊的過程來因應這種衰退:修復和回春。我所謂的「修復」,是指受傷後展開的細胞連鎖反應,它通常以發炎為特徵,隨後是細胞生長,以覆蓋傷害。而另一方面,「回春」指的是細胞不斷的補充,通常來自幹細胞或祖細胞庫,以因應細胞的自然死亡和分解。兩者─不論是幹細胞的數量或功能,都會隨年齡的增長而顯著減少,修復的速率減慢,回春的寶庫逐漸衰竭。
細胞生物學的未解之謎之一是,為什麼在成年後,有些器官可以修復,有些可以恢復活力,但其他的卻失去這兩種能力。造血幹細胞可以完全再生血液系統,但是神經元一旦死亡,卻幾乎不會再生出取代它的神經元來。有些器官則混合搭配這兩種過程,其中最複雜的或許是骨骼─它運用修復和回春來對抗衰老。可以修復骨骼的細胞在整段成年期仍然存在──儘管功能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大大減弱,然而形成關節軟骨的細胞也會隨年齡增加而急劇衰減。家母腳踝骨折,傷口雖然恢復甚慢,但仍然癒合了,可是她的膝關節腫脹卻無法逆轉,再也無法恢復到她童年時期輕易爬上番石榴樹那樣靈活柔軟。
原子彈促成死亡浪潮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上午八點十五分左右,在日本廣島市上空三萬一千英尺高處,一顆綽號為「小男孩」的原子彈從暱稱「艾諾拉‧蓋伊」(Enola Guy)的美國B-29轟炸機上落下。炸彈花了大約四十五秒墜落,然後在離地面島外科醫院(Shima Surgical Hospital)上方一九○○英尺的半空中爆炸,當時醫護人員正在工作,病人還躺在床上。炸彈釋出了大約相當於一萬五千噸黃色炸藥的能量─大約相當於三萬五千枚汽車炸彈同時爆炸。半徑超過四英里的火圈由震央向外蔓延,摧毀它所及的一切。街道上的柏油沸騰,玻璃像液體一樣流動,房屋灰飛煙滅,就好像被一隻正在焚燒的大手摧毀。在住友銀行的石階上,一名男子或女子轉瞬間就遭蒸發,只在被大火燒得發白的石頭上留下影子。
隨之而來的死亡浪潮共有三個波峰。七、八萬人─這城市近三成的人口,幾乎當場就遭烘烤死亡。「我嘗試要描述蘑菇〔雲〕,這股動盪的氣團」,轟炸機上的一名機尾砲手寫道:「我看到幾個不同的地方起火,就像煤床上噴出的火舌〔……〕看起來就像熔岩或糖漿一樣,覆蓋了整座城市,而且似乎向外溢流,進入山麓,流入小山谷,由那裡伸向平原,到處都竄出火苗。」
然後是第二波浪潮─來自放射病(最初稱為「原子彈疾病」)。正如精神科醫師羅伯特‧傑伊‧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所指出的,「倖存者開始發現自己罹患了奇怪的疾病,包括噁心、嘔吐和食欲不振,腹瀉並便血,發燒和虛弱,身體各部位因內出血而使皮膚出現紫色斑點……口腔、喉嚨和牙齦發炎和潰瘍。」
當再生與死亡失衡時
但還有第三波的破壞即將到來。受到最低劑量輻射的倖存者開始出現骨髓衰竭,導致慢性貧血。他們的白血球數異常波動,接著下降,在幾個月內暴跌,並崩潰了。如科學家厄文‧韋斯曼(Irving Weissman)和茱迪思‧靜流(Judith Shizuru)所言,「因最低致死輻射劑量而死亡的人幾乎可以確定是死於造血系統衰竭。」殺死這些倖存者的並不是血液細胞急性死亡,而是因為無法持續補充血液,血液恆定狀態的崩潰。再生與死亡之間的平衡傾斜了。這就像是意譯鮑伯‧狄倫(Bob Dylan)的歌詞:不在忙著出生的細胞就是在忙著死亡。
儘管廣島原子彈轟炸教人毛骨悚然,但它證明了人體擁有不斷產生血液的細胞,不僅僅是片刻,而是在整個成年時期,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如果這些細胞被殺死──就像在廣島那樣,整個血液系統最後就會動搖,無法讓自然腐朽的速度與回春的速度平衡。後來,這些能夠使血液恢復活力的細胞被稱為「造血細胞」,或「hematopoietic」──「幹細胞和祖細胞」。(摘自《細胞之歌:探索醫學和新人類》,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