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與白先勇老師攝於明星咖啡館。圖/爾雅出版社提供
作者與白先勇老師攝於明星咖啡館。圖/爾雅出版社提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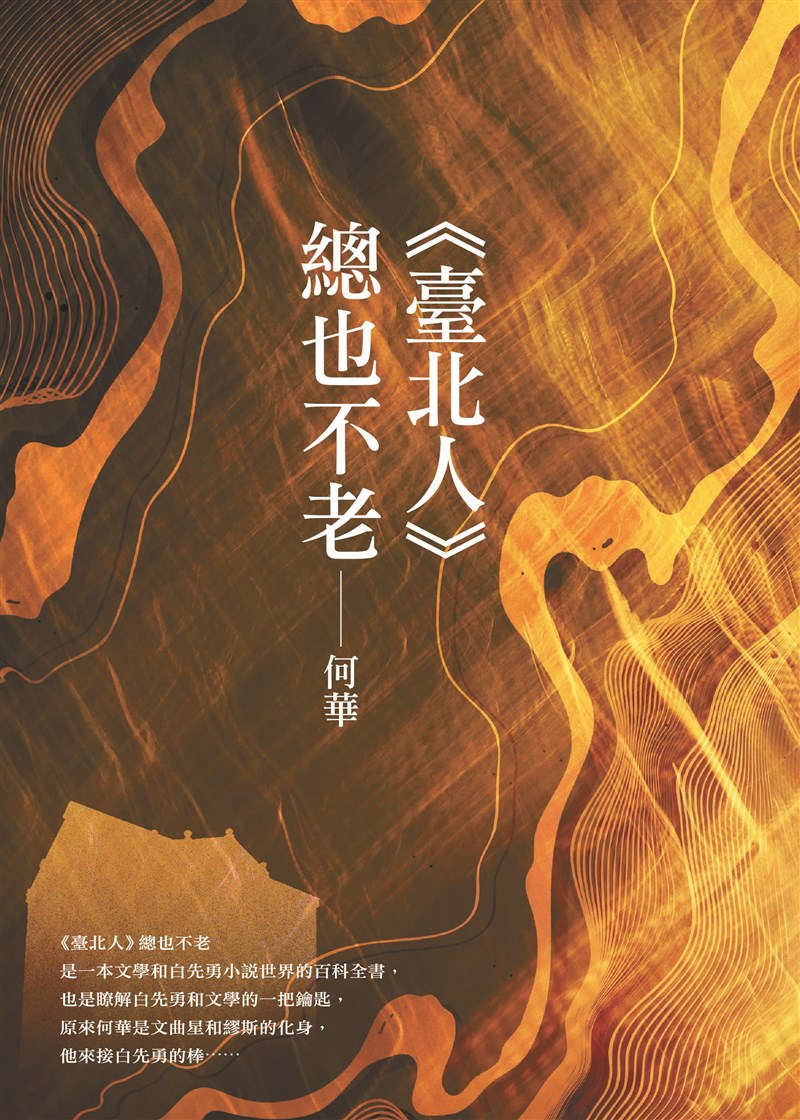 作者簡介
何華
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目前定居新加坡。文章散見《聯合早報》(新加坡)、《蕉風》雜誌(馬來西亞)、《萬象》雜誌(已經停刊)、《書城》雜誌、《上海文學》雜誌、《新民晚報》、《聯合報》(台北)、《明報月刊》(香港)、《三策智庫》(香港)。著有《因見秋風起》、《買金的撞著賣金的》、《老春水》、《一瓢飲》、《在南洋》、《南洋滋味》,以及首本繁體書《《台北人》總也不老》等。圖/爾雅出版社提供
作者簡介
何華
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目前定居新加坡。文章散見《聯合早報》(新加坡)、《蕉風》雜誌(馬來西亞)、《萬象》雜誌(已經停刊)、《書城》雜誌、《上海文學》雜誌、《新民晚報》、《聯合報》(台北)、《明報月刊》(香港)、《三策智庫》(香港)。著有《因見秋風起》、《買金的撞著賣金的》、《老春水》、《一瓢飲》、《在南洋》、《南洋滋味》,以及首本繁體書《《台北人》總也不老》等。圖/爾雅出版社提供
文/何華
佛茶,不是喝的。
雲南的茶花很有名,有一款「佛茶」更是名品。白先勇愛種花,尤愛茶花,他美國加州聖.芭芭拉的住家,院子裡種了不少茶花,包括佛茶,盛開時大美。說起來,佛茶還救了白老師一命。二○○○年盛夏的一天,他給一株佛茶培土時,頓感不適,心口悶痛,他放下工具立馬去醫院查看。醫生告訴他血管堵塞達百分之九十九,隨時有心肌梗塞而致命的危險。當天,白先勇就在醫院裡做了心臟搭橋手術,「撿回一條命」。白先勇與佛有緣,連救他命的茶花都叫佛茶。
說到這段往事,白老師連連感恩佛菩薩,他說就在二○○○年六月,他去日本京都參觀了「三十三間堂」,裡面供奉了一○○一尊觀音塑像,震撼力之大,無以言表。白老師說:「走進去,在中間那尊觀音前,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那一刻,我皈依的心很強烈。回到美國,有一天去給佛茶培土,隨即發現了病兆,好像冥冥之中,觀音菩薩在保佑我。」他的老朋友歐陽子說:「是一○○一尊觀音把白先勇的命拉了回來。」兩年前,我去京都,也去三十三間堂朝拜觀音群像,還請了一塊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牌送給白老師。
自小埋佛根
實際上,白先勇的家族信奉回教,可他多次表示自己的宗教情感是傾向佛教的,他自小就埋下了佛根,至今床頭邊還放著《觀音勤行儀》,外出住旅館也不例外。
二○○四年,青春版崑曲《牡丹亭》在蘇州大學存菊堂大陸首演,演出前一天,我陪白老師去靈岩山拜佛。近代高僧印光大師曾駐錫靈岩山,長期以來靈岩山保持著純正道風,而且幾代住持一直不修盤山公路,若你有心來此,就必須靠自己的雙腳拾階而上。
那天白老師和我一步一步登上山,法喜充滿。白老師跪地拜佛,讓我聯想到《紅樓夢》裡的寶玉出家。白先勇不像很多人(包括張愛玲)一樣貶低後四十回,他認為後四十回寫得同樣出色。張愛玲不信佛,她對寶玉出家很可能無動於衷。另外,一○六回「賈太君跪地禱天」,賈母大紅拜墊上那一跪,那一番念詞,真個令人動容。想必張愛玲對這一節也沒有特別的觸動。張愛玲是我非常推崇的作家,但她沒有宗教感情這一事實,不能不說少了一股「動力」,文學山峰的最後幾個台階她乏力了,上不去了。
這幾年,每次去台北見白老師,他總帶我去明星咖啡館坐坐,聽他談藝文舊事,不亦樂乎。有時他也帶我去寺廟燒香,二○一五年去台北,我們去了龍山寺,那天是個大日子,人擠人,熱鬧非凡,白老師就在人堆裡點香拜佛,一如凡夫。白老師也坦承,他對紅塵還有幾分留戀,做不到百分百看破放下。正是對紅塵的幾分留戀,拉近了白老師和我們的距離。(摘自《《台北人》總也不老》,爾雅出版)
作者簡介
何華
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目前定居新加坡。文章散見《聯合早報》(新加坡)、《蕉風》雜誌(馬來西亞)、《萬象》雜誌(已經停刊)、《書城》雜誌、《上海文學》雜誌、《新民晚報》、《聯合報》(台北)、《明報月刊》(香港)、《三策智庫》(香港)。著有《因見秋風起》、《買金的撞著賣金的》、《老春水》、《一瓢飲》、《在南洋》、《南洋滋味》,以及首本繁體書《《台北人》總也不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