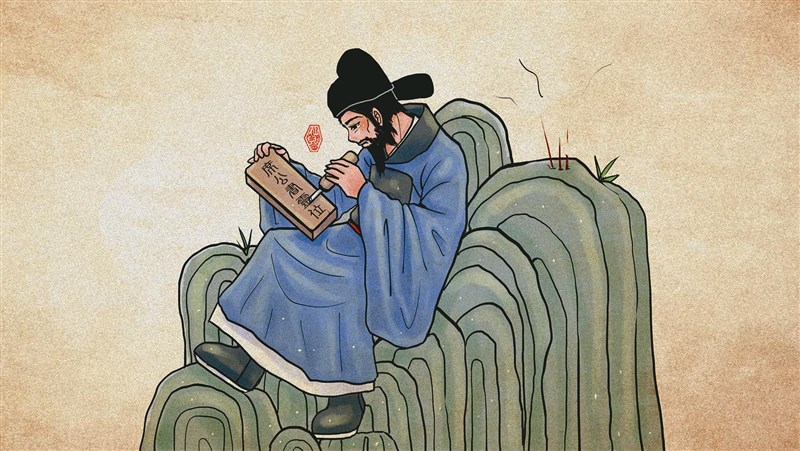 圖/陳復提供
圖/陳復提供
文/陳復
因為席書的隆重聘請陽明主講文明書院,使得困在淺灘的龍終於翻身了。席書長期對陽明的無條件支持,更表現在嘉靖時期他曾經強烈跟皇帝推薦陽明進內閣主持國政,他在奏疏說:「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大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剛正不阿的席書,能有如此性情流露,不惜說出其餘大臣論資質都只是「中材」,匡正世局「非守仁不可」,反映出他對陽明智慧與才幹的無比推崇,儘管明世宗對此未置可否。
當嘉靖六年(1527)席書過世,陽明特別寫一篇〈祭元山席尚書文〉,他不禁遙想當年,發如此感慨:「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為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淪落到荒野的陽明,對當年席書的賞識,甚至還跟他拜師求教,實在心底有無法言喻的滋味,他聽到席書過世的訃聞,在千里外設牌位祭奠,雖自慚不能有益於君國,但發願將更精進於我們共有的心學,希望最終「不負知己」的恩情。
如果各位看官已經能體會陽明龍場大悟的低階版,就讓我們再回過來認識龍場大悟的高階版,因為這樣才能讓各位看官瞭解席書為何會對陽明如醉如痴到無法自拔的程度,陽明的奇魅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陽明的思想有如曼陀羅般不斷環繞前行,正德三年(1508)他領悟到「吾性自足」,隔年他就更豐富這個觀念,使其拓展出後世熟知的「知行合一」,《王陽明年譜》記載:「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這是來自於去年的冥契經驗的繼續深化,而在認識論層面的嶄新闡發。
「知行合一」這個觀念歷來受到極大的誤解,最常見的陋見是指稱「理解與實踐要能合一」,這種說法現在已經家喻戶曉,各位看官如在街上拉一位角頭老大來請教一番,他都會覺得如果自己承諾什麼黑白事情,最終說到沒做到,就會對小弟面子掛不住,因為裡頭有「知行不合一」的問題。然而,這種說法只是種極其淺白的語意,還需要陽明歷經九死一生的龍場悟道後,特別再來跟各位看官聲稱陽明有這款主張嗎?顯然這裡還有更深層的義理,否則就是故做玄虛了。
如果我們由冥契經驗的角度來認識陽明說的「知行合一」,重點在「合一」具有甚深奧祕,這個「一」(the One),就是指整體(the Whole),其實就是指藉由體驗來回歸本體,「知」與「行」則都是回歸本體給出的呈現,其間體驗自會給出人的理解與實踐,理解與實踐則具有共生性與同質性,或許有現象的先後,卻沒有脈絡的先後,因為理解本身就是某種實踐,實踐本身就是某種理解,它們都是本體的已發,本體的未發則在那冥契經驗的領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