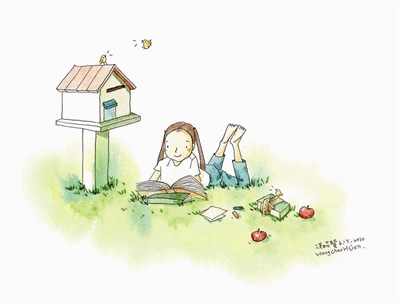 時至今日,傳統出版業者苦嘆營收節節敗退,原因仍不脫受數位平台的重創,不知該如何回應才好,畢竟,業績低迷是事實,只是,歸因於「數位平台」,是否過於簡單了呢?繪圖/洪昭賢
時至今日,傳統出版業者苦嘆營收節節敗退,原因仍不脫受數位平台的重創,不知該如何回應才好,畢竟,業績低迷是事實,只是,歸因於「數位平台」,是否過於簡單了呢?繪圖/洪昭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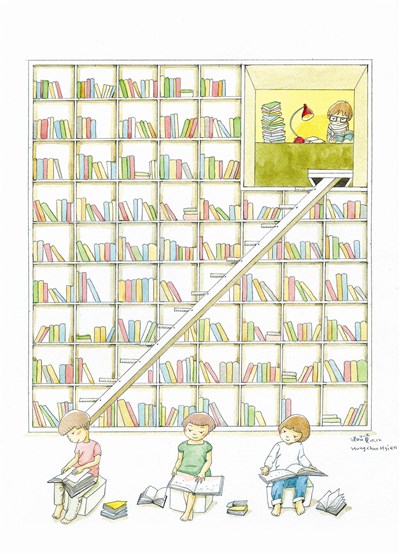 時至今日,傳統出版業者苦嘆營收節節敗退,原因仍不脫受數位平台的重創,不知該如何回應才好,畢竟,業績低迷是事實,只是,歸因於「數位平台」,是否過於簡單了呢?繪圖/洪昭賢
時至今日,傳統出版業者苦嘆營收節節敗退,原因仍不脫受數位平台的重創,不知該如何回應才好,畢竟,業績低迷是事實,只是,歸因於「數位平台」,是否過於簡單了呢?繪圖/洪昭賢
文/朱玉昌(元智大學中語系兼任助理教授)
時至今日,傳統出版業者苦嘆營收節節敗退,原因仍不脫受數位平台的重創,不知該如何回應才好,畢竟,業績低迷是事實,只是,歸因於「數位平台」,是否過於簡單了呢?
冤有頭債有主,既然點名數位平台是元兇,就該好好抽絲剝繭,仔細瞧瞧這名數位先生究竟有多神!
數位平台是以資訊科技為經,將大量內容複製儲藏於肉眼看不見的虛擬空間為緯,再藉由一個視屏接收載體傳遞給大眾,形貌可以是圖文閱讀、影音視聽、互動遊戲、資訊儲存與搜索、出版典藏和學習、金融服務、生活行動雜項購買、即時溝通……等,幾乎涵蓋人類多重習性,隨取隨用,便捷到改變了人類數千年的行為模式。
照這樣看來,數位平台影響至極至廣,殺傷力強,遭波及產業面臨風燭殘年,紙本出版首當其衝。但務實論出版處境,自一九八七年美國作家朱迪.馬洛伊(Judy Malloy)推出人類史上第一本符合虛擬意義的電子書《羅傑叔叔》(Uncle Roger)開始,到二○○七年亞馬遜網路書店賣出第一台Kindle電子書閱讀器為止,時隔二十年,數位出版大軍正式大舉進攻,「紙本書將走入歷史」的說法才甚囂塵上。
在亂局中,各種揣測如流言四射,人非先知,豈可妄下斷論。新事物發展,皆有規律,須經一段區間,才能逐次明朗。過程中,新事物建設者,掌握新穎關鍵技術,設法攻城掠地勢所難免,舊事物經營者,當不得自亂陣腳,應觀其變,研擬對策,在新事物能否全盤取代舊事物前,全力鞏固並維繫人心之所繫,即便有朝一日舊事物遭新事物全面替代,深信,舊事物經營者已能找出萬全的解套方案。
數位出版也有天敵
果然,數位出版同樣有天敵!那股在美國勢如破竹的績效,火紅般的光景,不出五年,專家預估值紛紛破局,一路疲態盡現。數位出版固然有良好發展條件,仍須克服技術上實質獲益的障礙,重點瓶頸更在於人類的「有限時間」和「感覺需求」。因為時間有限,數位平台其他功能瓜分可用時間;因為感覺需求,電子書冰冷的文字,無法滿足實體觸覺所給予的溫暖。
按理出版人作書成精,應當熟悉黑暗深淵裡,總有一處相對光明的角落,這會是絕處逢生的希望。那麼何不重新認識自己所生產的書呢!
何謂「書」?書是印有文字或圖像的本子,是由墨水、紙張或其他材料固定在書脊上的組合物,是一頁頁觸摸得到、聞得到,具備保存價值的千年歷史性文明資產延續。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其所下的定義:「凡由出版商出版,不包括封面和封底在內四十九頁以上的印刷品,具有特定書名和著作者名,編有國際標準書號,並有定價並取得版權保護的出版物稱為圖書。」
就字義解釋,「書」指的是實體。「電子書」雖也列位現代人廣義的通稱而納入「書」的範疇,但功能僅作方便於知識索取與增加「閱讀」樂趣的工具,這本虛擬抽象的書,並非真正的「書」。
不只出版樣樣難做
回顧去年底出版產業發布的〈二○一四博客來報告〉,博客來指稱二○一五業績將持續增長,這是通路趨勢上的勝利,此刻,年尾將至,也時有所聞某出版社已興高采烈地籌畫著開春後犒賞員工的國內、外旅遊行程,這是做對產品的結果。因此,紙本書只要有優秀作品配合正確銷售管道,出版者稍懂得盤算供需原理,掌控住柏拉圖最適(Pareto optimum,指資源分配的一種理想狀態)效率,那麼,再壞的時代,都會有脫穎而出的績效。
過去十年,台灣出版產業總體新書年均出版量維持在四萬種水準,活絡於經常稅運作的出版社家數也保持在一千七百家左右(立案登記平均家數則約一萬三千家),差距不大,紙本書和電子書兩者在市場上雖然存有載體不同、內容相同的競爭者關係,數位銷售始終對紙本銷售影響有限。
然而,出版總體產值卻硬生生攔腰斬半,這固然與數位平台發達有直接關係,更多因素是整體社會氛圍所造成的人心思變。
科技快速變化,成就了分眾多樣式選擇,紙本書與電子書無可避免地如同其他類別產業所面臨的困難一樣,除了同業、同質競爭,還有更龐大的替代性異質誘因競爭,嚴格說來,現在不是出版難做,是樣樣難做。
或許,業者朋友真該想想《尚書》中提及的「民之所欲,天地從之」的精神,若能理解並扣緊這句話,不安的憂慮自得一番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