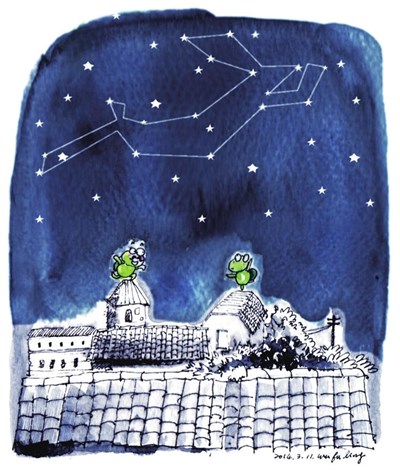 圖/吳馥伶
圖/吳馥伶
如同家人般的兔子毛球,有個深夜突然下半身不能動了,經過「非犬貓科」動物醫院的兔子獸醫的診治才慢慢脫離危險期,兒子小烏龜也較能接受一天到晚哭紅雙眼的媽媽(小烏龜無法感受媽媽是因心疼毛球而哭),學著我蹲在圍欄邊童言童語親切地問毛球要不要尿尿(抱起牠擠尿)?要不要喝水水(拿湯匙把水送到嘴邊)?要不要吃草草(一根根地餵著)?要不要按摩(幫忙翻身按摩身體)?這些關照他人的對話,從語言的選用到實際付出行動,兩者的配合對小烏龜是困難的,但他仍認真觀察、模仿我的動作和說些安撫毛球的話語。
當療程繼續著,有天兔子醫生說毛球很有進步,接下來可以考慮用針灸及吃中藥來幫牠復健,等牠的後肢能承受自己的重量時,就可以開始考慮「助行器」了。
聽到「助行器」,烏龜爸爸和小烏龜商討著,但各自腦海裡浮現各自的設計圖(不知是何原因,小烏龜從小跟爸爸就有很大的距離感,對他,爸爸是住在一起的陌生人)。
這天下午,烏龜爸爸帶著小烏龜逛特力屋買零件,為了幫毛球打造兩人想像中的兔輪椅。父子商量老半天,買了網架和活動輪,兩人在工作室裡進進出出穿梭於不同機台中,車車削削地又是鑽孔又是試螺絲、螺帽。結果回家讓使用者測試,毛球不但不賞臉,更不肯待在車上。
挫敗的小烏龜「教訓」著毛球為什麼不肯接受、使用「輔具」?叨叨對毛球念著:「這樣子移動就不用拖著後腳辛苦地爬,不是比較方便嗎?」對著失落的小烏龜,我要他換個角度想(站在他人立場思考,這對星星兒還真難):如果你是剛受傷的毛球,讓你拖個長長大大的不明物體在身後會是怎樣的感覺?況且腰椎受傷的毛球自己都還不能支撐自己的狀況下,感覺上會不會像是被怪獸追趕,嚇死牠了呢!
小烏龜失落卻平靜地接受兔輪椅的失敗,但我卻高興他和爸爸經由毛球事件,而搭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