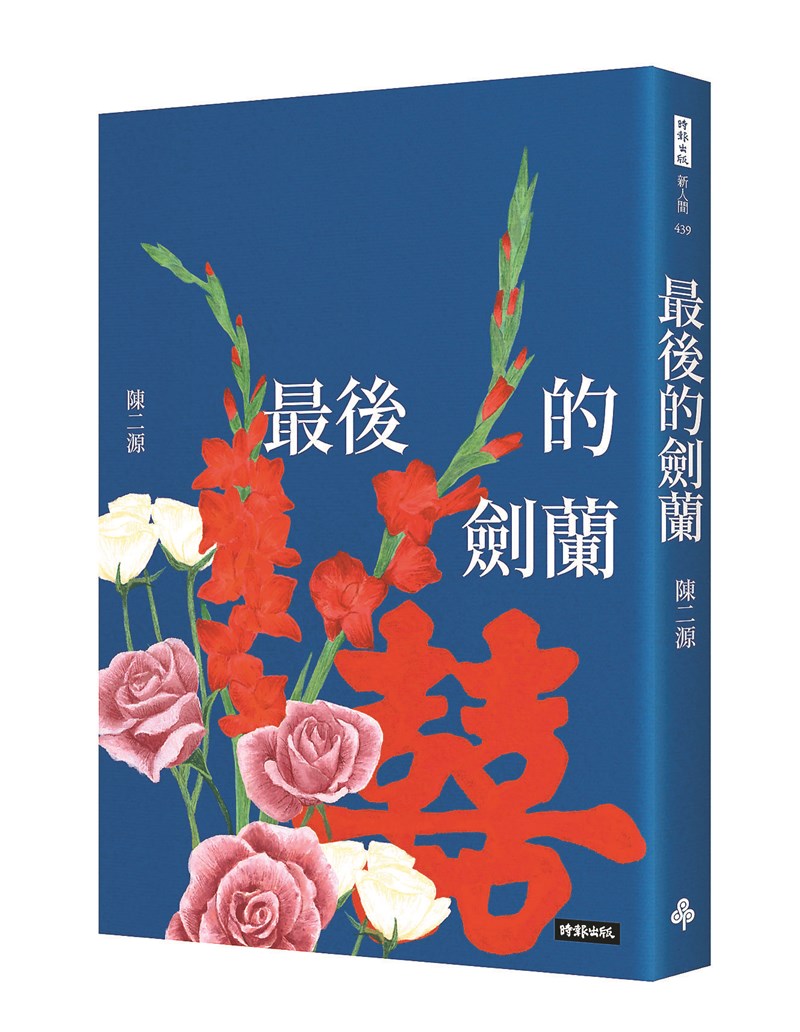 圖/時報出版提供
圖/時報出版提供
文/林楷倫
我曾經幻想家裡的陽臺能變成人造叢林,抱著巨大的鹿角蕨遮住臉說:「這是我的兒子。」
種過幾種網路說超好種的植物,小天使、大天使等等,沒多久枯萎死亡。那年,龍舌蘭科的觀葉植物在觀葉社團裡價格飛漲,是鬱金香狂熱嗎?那年我也剛認識陳二源,我截一張被炒作的虎尾蘭問他有沒有(分明想A一盆),他說有,且立刻傳了張照片給我。
那張照片是花田圍牆邊幾株虎尾蘭。他問我還要不要其他種類?金邊?銀后?
其實他問的其他種類,我都聽不懂,但小孩才做選擇,我全都要。
我仍怕種死,二源只說:「當野孩子養,這批植物本來就是野生孳長。」
我沒跟他說過這批植物後來長得怎樣,就算說了,他也會說野孩子自己長大很自然呀。
對,植物的模樣本來就是自然的。這句話如果出於一名花農之子,或許奇怪,就像魚販說多吃魚才能保育海洋。《最後的劍蘭》可以用許多的角度去切入,如職人面貌、男性、更不用說以文學的角度。倘若不知道陳二源的背景,一翻開這本書也能知道他的背景,花農之子。陳二源展開不同於近年的職人寫作(包括我),除了職業不同,更不同的是切入的方法。他不是幾近暴力的自我揭露與復仇,沒有過度的溫情與勵志。他透過種植物表達情感,有殘酷有痛苦,也常有感謝,其他職人寫作當然也有。
《最後的劍蘭》給予的是內斂且質純的溫柔。
所有殘酷的痛苦的場景,陳二源都放在處理植物的瞬間去述說。看我如此說,會以為這些情感很折繞,不,其實直接。〈銹病〉裡寫父親的中風與農災,那些毀壞的農舍與近死的植物,打掉重練埋入土裡,這悶痛的故事樣貌是成長的模樣,銹病結尾的短短兩頁間,將心血埋入土裡承認死亡,轉向,重生。
如此細節的調整,不外乎說的是絕望然後呢?不是希望,而是繼續生活。
「站在空無一物的田中央,我想像著,埋下新的種子,一年後從母葉上分芽而出,新的,已經是沒有銹病的電信蘭葉。」(〈銹病〉)
在農田小小的交友圈,以農務為主,環繞的生活是家族生活。《最後的劍蘭》有許多書寫父親的篇章,陳二源展現的父親樣貌與臺灣文學常出現的「沒有用的老爸」完全不同,可以見到父親的柔軟,或是這麼說,陳二源細寫的是「男人」,從〈心〉寫矛盾於農務與農會改選的權力的男人,並不是刻板的直接推向兩極,二源的角色往往是位在中間,做什麼都不是又做什麼都對的模樣。
人總是要選擇的。
選擇美的植物,選擇「更上一層樓」的人生,選擇自己或是家族。
卻,我們大多遇到這些選擇時,想著時間會度過一切。
人的樣貌這般展開,有時像是無所適從的孩子,有時是任性的王。
《最後的劍蘭》裡的步調是自然植物般的,被選擇或是自己選擇,都是因果,也只能接受。
《最後的劍蘭》有令人舒適的閱讀感,貼近於臺灣這片土地,異於都市生活的時間感,一切都是慢慢來比較快。在農村的人們日光照射,風吹雨淋,等待成長。離鄉的人們免不了被擔心被追問何時歸根。在陳二源的筆下,人類是在工作裡變化生活,生活中仍是工作,重點是工作不是苦難,是一個家族是一片土。《最後的劍蘭》是鄉土,但沒有與城市競爭的二元對立,《最後的劍蘭》是職人,但沒有賣苦賣痛賣底層。
「人都是這個樣子的。」(〈夕色〉)
在悠緩的日常生活間,探問各種細小的困境,解決不解決都牽動下幾秒的人生。我們都能讀懂《最後的劍蘭》裡頭的事件,一臺新的吹風機能讓人開心,一株枯腐的植物讓人憂鬱,其實幾天後就忘了,不過,小說家是虛構生活的剪接師。陳二源裁切他想說的,語速不快,柔緩地說這本他的小說。
這本小說很美,最美的是平凡。
「他已經找到自己暗暝的日頭了。」(〈暗暝的日頭〉)
這句話作為結尾,滿滿是土是草與花,是乾淨的野孩子。
送給仍創作的二源與閱讀的你們。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最後的劍蘭》一書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