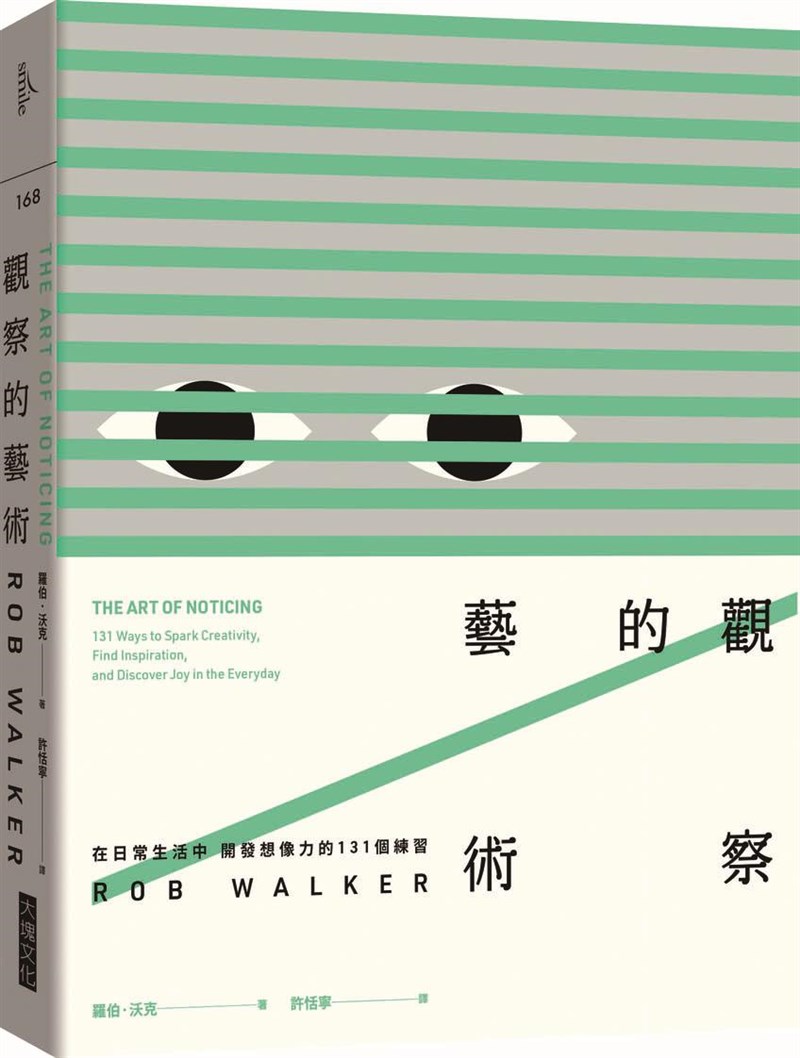 在這個手機、電腦讓人分心的年代,人們通常失去了體驗當下、活在當下的能力。專欄作家羅伯.沃克藉著《觀察的藝術》一書,想喚醒大眾的感官,更重要的是以全新的方式看世界。 圖/大塊文化提供
在這個手機、電腦讓人分心的年代,人們通常失去了體驗當下、活在當下的能力。專欄作家羅伯.沃克藉著《觀察的藝術》一書,想喚醒大眾的感官,更重要的是以全新的方式看世界。 圖/大塊文化提供
文/羅伯.沃克
重新思考第一印象
藝術家羅伯特.爾文絕對是支持觀察的模範人物。如同勞倫斯.韋施勒(Lawrence Weschler)在《看,就是忘掉看的東西的名字》(Seeing is Forgetting the Name of th Thing One Sees)所言,爾文的作品聚焦於觀看的體驗與脈絡,重點不在於打造藝術品,而在於「讓大眾意識到自身的感知」。
爾文起初是畫家,但花很多時間盯著畫布,什麼也不畫。他極度在意作品展示空間中的各種細節,如角度、地板、燈光。有一次,爾文在西班牙整整待了八個月,沒創作任何作品。
「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點一段時間之後,我找到某種力量。」爾文告訴韋施勒:「過了一陣子,你彷彿剝去那樣東西的外殼,有辦法進入更深層的邏輯,找出這樣東西是以什麼樣的方式產生意義。」爾文的創作素材日後逐漸轉移到壓克力板,把光當成媒介,創作出「隨場地變化」的作品。爾文的裝置藝術改變了我們看待空間的方式。
我們可以借用爾文的作法,改成人人都能應用的練習。「慢速藝術日」(Slow Art Day)就是一個例子。其官網SlowArtDay.com的介紹指出,這一年一度的活動在全美各地舉辦,參加者在博物館集合,「觀看五件藝術品,一件看十分鐘,接著在午餐時間集合,討論剛才的體驗。」
你不必等到下一個慢速藝術日到來才這麼做。花那麼多時間看一件藝術品非常有趣,但你也可以選擇地區大賣場的五項商品,一個看十分鐘。
慢慢看,聽起來簡單,但其實是很前衛的作法。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一項研究發現,遊客平均會在每幅畫作前面待十七秒。從慢速藝術日最基本的十分鐘往上加,你將一窺是什麼引發了爾文發人深省的觀照過程:你將看見自己原先忽視的細節,找出新的連結,重新去思考自己的第一印象。
重新框架熟悉事物
我的另一位學生露西.諾普斯(Lucy Knops)受到藝術家爾文的觀看習慣啟發,思考如何框架自己看見的東西。她用可以重複書寫、擦拭的壓克力板,製作拍立得大小的實體相框──就像是可攜式的窗子。諾普斯解釋用法:「拿起這個框,對準一樣東西或景物,在上頭寫下一、兩個字。」例如:漂亮、空白或多雲。
「接下來,」諾普斯繼續說明:「把框對準其他東西,但留著原本的描述。」先前的描述如何影響了你這次看到的東西?
以上的點子與柯麗塔.肯特修女(Sister Corita Kent)的作法有異曲同工之妙。肯特修女是修女,也是藝術家。她在《用心學習:釋放創意靈魂的方法》(Learning by Heart: Teachings to Free the Creative Spirit)一書中,鼓勵大家拿幻燈片的片夾當「立即取景器」。你也可以自製;在厚紙板上切割出一個長方形的洞,用來縮小或重新框架你的視野。「這個取景器可以協助我們跳脫情境。」肯特與合著者簡.史都華(Jan Steward)寫道:「我們得以為看而看。」
用超慢的速度看
珍妮佛.L.羅伯茲(Jennifer L. Roberts)在教藝術史的時候,要求學生用「久到令人痛苦的一段時間」觀看一幅作品。究竟要看多久?答案是三小時,也難怪學生抗議。
「人們通常以為視覺是瞬間的。」羅伯茲寫道:「看,感覺上是直接、不複雜、瞬間完成的動作—據說這是為什麼在當代的科技世界,視覺成為傳遞訊息時最主要的感官能力。然而,學生做這項作業時,本能就學到,任何藝術作品都一樣,某些細節、規律與關聯需要花時間才能夠察覺。」
羅伯茲指出,她的學生不再那麼抗拒那份作業之後,發現非常、非常緩慢地觀看,讓自己不得不注意到一開始忽略的事,有時甚至整個改變他們對於作品的理解。緩慢觀看的過程,會開啟第一眼沒注意到的意義與可能性。
除了凝視藝術品,這個作法也可以應用在其他場合。用真的很慢、很慢的速度看著任何東西,八成就會看見意想不到的豐富世界。
(本文摘自大塊文化出版《觀察的藝術:在日常生活中開發想像力的131個練習》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