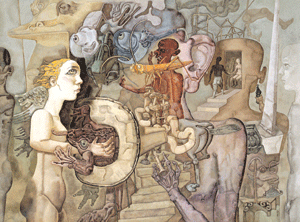
他的內在澎湃,但是囚禁在那個失能的,永遠「昏睡」的軀體之內。那個無能的,對於真實世界,對於外在世界無能駕馭的身體,便是他永遠醒不過來的惡夢。
在與心理師諮商時,他說到通常人都有兩個面相。一個是「Ⅰ」,那是對外的形象,也是社會上對這個「我」的看法;另一個是「me」,那才是自己必須面對的真正的自我。
我們的秘密,隱私,真正的狀態,不可告人或不想告人的部份,都是在面對這個「me」的時候。我聽他這樣說,就覺得:這個「me」,雖然是小寫,其實比大寫的「Ⅰ」,更巨大吧。
一個人的「Ⅰ」和 「me」太貼近的時候,可能會受到傷害吧!被外在世界所傷害。「Ⅰ」和 「me」太貼近的時候,就是無防狀態,無保護狀態。也許給人家帶來麻煩,因為他把保護自己的責任賴在別人身上。
●
最近在看顧城。
顧城是中國著名的現代詩人。八歲開始寫詩,之後便滔滔不絕,寫到了死。他最高紀錄是兩天寫了八十四首。是在追求他的妻子謝燁的時候。
他的詩公認是純淨,透明,純潔無塵的。他寫詩像小孩子說話,完全沒有戒心,信任面前所有的閱讀者,把自己的真心掏肝扒肺的獻出來。
他著名的詩句: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還有,寫愛情的:
我想畫下早晨,
畫下露水所能看見的微笑,
畫下所有最年青的,
沒有痛苦的愛情;
畫下想像中,
我的愛人,
她沒見過陰雲。
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顏色,
她永遠看著我,
永遠,看著,
絕不會忽然掉頭而去。
我看他的末四句,忽然非常傷感。我們對愛情所求其實就真只是這樣單純。
只是:
她永遠看著我,
永遠,看著,
絕不會忽然掉頭而去。
不過,一個專注的,永遠的凝視,根底上就不可能是人間的吧!
這樣的顧城,他的內在是怎樣,外人眼中的他就是怎樣。所以顧城成為一個被容忍,但是沒有人受得了他的,天才。外界說他不懂實務,完全沒有自理能力,離開了他的妻子謝燁,就連想寫詩的時候,紙和筆在那裡都找不到。
他脾氣特壞,心情不好就掀桌子。有次飯桌上吃飯,岳母說了什麼話惹到了他,當場他就把正在吃的一碗麵倒扣到岳母頭上。
他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除了他的天才,一無所能,一無所有。
與其說他像一個被慣壞的孩子,我覺得他像一個從來沒有被馴養成功的野獸,所有的反社會人格大約多少都是這狀況,他們沒有被馴養的成分比馴養的部分多的多。他們被扔到人類世界來,許多的格格不入,許多的不適,甚至,許多的痛苦。某方面來說,我覺得顧城有點像醒著的「植物人」,他的內在澎湃,但是囚禁在那個失能的,永遠「昏睡」的軀體之內。那個無能的,對於真實世界,對於外在世界無能駕馭的身體,便是他永遠醒不過來的惡夢。
一九九三年十月九日。在紐西蘭的激流島,顧城的妻子謝燁要離開他,於是顧城用斧頭砍殺了謝燁,自己上吊身亡。
時年三十七歲。
●
顧城的「Ⅰ」和 「me」,可想而知是非常貼近的,簡直可以說是渾然成一體。
通常我們的自我矛盾,都是「Ⅰ」和 「me」之間出了問題。
我們的「me」,一定是最放鬆的,最舒適的時候。但是在「me」裡的自安狀態,有時候是不見容於大社會的。都未必是黑暗面,有時候甚至不過是一種天真,沒有惡意的直率。高興就笑,悲傷就哭,生氣就發怒,發現自己的「東西」被奪走了就要搶回來;這難道不是天真和直率嗎?小孩子不都是這樣嗎?然而我們的大「Ⅰ」這樣天真的話,一定會出事的。就連面對最親密的兩人關係,也一樣會出事的。
想到佛經裡說要調伏自己的心,如調伏洪水猛獸。讓自己的「Ⅰ」和 「me」非常貼近,那個無保護狀態,可能是一種無賴,要別人為自己負責。因之要調伏的是「me」吧。要學習的是「me」吧。讓那個「me」與大世界相容,讓「Ⅰ」和 「me」都成為自己的「本來面目」,便與自己和解了,也與世界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