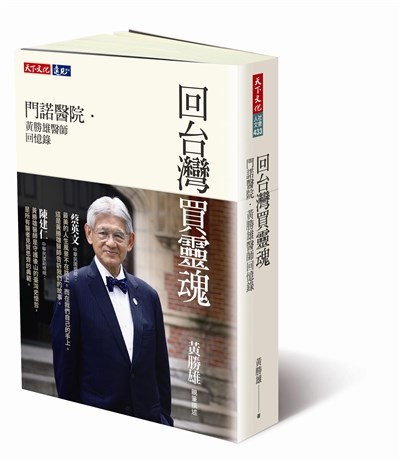 《回台灣買靈魂—門諾醫院黃勝雄醫師回憶錄》
作者:黃勝雄
出版社:天下文化
《回台灣買靈魂—門諾醫院黃勝雄醫師回憶錄》
作者:黃勝雄
出版社:天下文化
文/黃勝雄
二○一四年三月十三日,剛好是我七十五歲生日的那一周,我替一位從彰化到花蓮的基督徒弟兄開再發性的惡性腦瘤刀。第一次是兩年前,術後他有好品質的生活。這次開刀準備做化療,也惋惜這位弟兄才五十多歲,恐怕剩下的歲月不多。這次的手術也使我決定,這是我當神經外科醫師四十年生涯的最後一台刀。不是我的體力或眼力忽然下降,而是我發覺自己逐漸失去耐心,很不想再接受挑戰的心境油然而生,我更擔心以後會造成困難或傷害病人。
本來是安排早上八點下刀,卻因為麻醉沒準備好,延誤了半個小時。
在手術進行中需要用微小螺絲起子把上次用來固定頭蓋骨的小螺絲鬆開,才能進入腦部開刀。但是這次的開刀團隊找不到工具,又叫我乾等了半個鐘頭以上,接著是開刀進行中當我專注在顯微鏡下的視野伸手要儀器時,刷手護士三次遞錯了器械,使我無法順利進行,因而感到不耐。心想,如果是動脈出血怎麼辦?以前配合的刷手護士得心應手,我伸手她們就知道遞上什麼器械。現在也許是我和她們已經產生代溝?是的,我的年齡是她們的三倍大,當然有代溝!或是我用英文指令她們聽不懂?(應該也是)或是她們的工作倫理開始變質了?但不管什麼原因,我已經開始緊張沉悶。
只好默默地壓下自己的情緒完成手術。無奈之外更不能忍受這種工作上的不順暢,最後完成手術時間比原先預期多兩個小時,還好病人送到加護病房後都很平安。
我回想在美國二十五年來,開過六千台刀,來台灣二十年最少也開了兩千台刀,從來沒有這麼挫折。以前一定也有過不順暢的經驗,但為什麼這次讓我這麼樣難過呢?我的結論是,因為我已經老了,也沒有一個好的團隊了。
讓後輩學到智慧
在北美洲的眾多神經外科醫師中,不曾有人寫過最後一台刀的心路歷程。很可能是在全美執業的神經外科醫師不多(估計每八十五萬人口才一位)在社區能互相支援的機會幾乎不可能,使他的職務無人能取代(除非在醫學中心有兩位以上的神經外科醫師),最後他們不是工作上過勞死,就是因病不能再執刀而被迫停業。倒是有一位密西根大學神經外科主任Edgar Kahn醫師鑑於他的老師Max Peet在工作中忽然心肌梗塞死在醫院,他就在一九七○年悄悄安排退出緊張勞心勞力的工作,而後寫了一本《一名神經外科醫師的日記》陳述他的生命經歷及準備退休的經過,讓後輩的我們學到了他的智慧。
同樣的事也發生在我的指導老師L. Olmedo醫師的身上:L.O老師和我在半夜開完了急診刀,本來應該回家休息,但他的愛心和熱情邀請我到他家吃晚飯。當時是八月的凌晨一點,吃完他的料理送我回醫院時已經是早上五點鐘。我還年輕是第三年住院醫師,在值班室小睡到七點又開始一天的忙碌工作,而他,卻在這天的下午因心肌梗塞送來醫院,死在大家的眼淚和嘆息中。
這對我衝擊很大,因為他一直待我很好,把我當成自己的徒弟。他也是Max Peet訓練出來的徒弟,他們這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情懷令人尊敬,但是他太年輕了,只有六十二歲,實在很不忍。我心想我以後寧可學習Kahn教授的智慧,知道什麼時候該開始打烊。這對任何一位名望如日中天的外科醫師都是很困難的決定,是需要智慧的。(本文摘自《回台灣買靈魂—門諾醫院黃勝雄醫師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