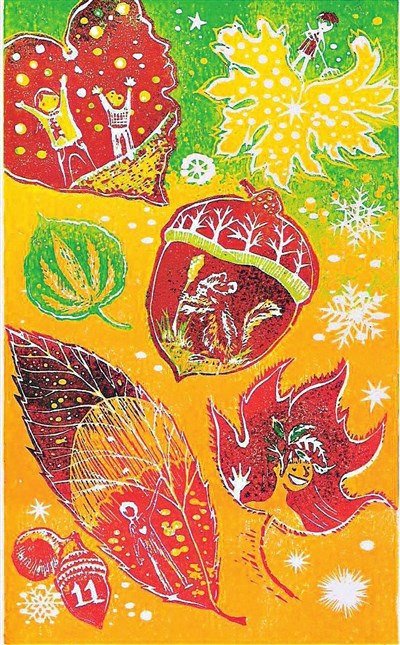 我不浪漫已經很久了,掂著這玉石材質顏色都不錯,想著將字磨去,還是一枚好印章。圖/劭嫻
我不浪漫已經很久了,掂著這玉石材質顏色都不錯,想著將字磨去,還是一枚好印章。圖/劭嫻
我不浪漫已經很久了,掂著這玉石材質顏色都不錯,想著將字磨去,還是一枚好印章。
「我們買杯飲料吧!」輕揚的喜呼。從我身後走過,年輕、短髮,兩個走路都是外八的胖女孩。
這一刻,真是浪漫。我打賭她們不會薑茶烏龍綠去冰去糖如我,極大可能直接下的就是大杯珍奶,這條路三百公尺內有四家飲料
店,她們過了這第一家的魔考也捱不過第二家,乾脆就當下果決。
與十八世紀歐洲的藝術文學無關,我是指那情感不被任何理性束縛,力道噴薄而出的華麗剎那。R o m a n c e!誰不知道該減肥。
浪漫有左鄰也會有右舍,它左邊住真率直抒,另一邊緊鄰的一定是無聊沒用。我從抽屜深處翻出一枚玉石印章,上頭是四個楷體字,涵安浩正,我孩子的命名末字,備全了兩男兩女以便敷於使用,後來終我一生只用上一個。
那時我剛結婚,生活裡存在很多理所當然,元宵夜要提燈籠去散步,假日牽手上市場,天天都相見了也仍要有愛情浪漫,而浪漫是雙人舞步,需要另一個人配合和成全。
這印章我現在看來是花錢無聊占空間,真不懂當時我怎麼會有這樣幼稚的念頭?但它好像完全寫實傳真了一個二十五、六歲幸福新嫁娘的無邪浪漫,生了這個再生一個、或再一個,是女的就這個,是男的就那個,兒兒、女女、兒女、女兒都沒關係,我們全都備好著等著迎接哪,這不就是這麼過下去的天長地久嗎?我不浪漫已經很久了,掂著這玉石材質顏色都不錯,想著將字磨去,還是一枚好印章。
另一個篆刻的玉石印章,是我發想為簽書落款,專為我的讀者而刻,上有四字:歡喜結緣。出第二本書時辦過兩場演講後的簽書會,一場在高雄,一場在台南,高雄那場門可羅雀,台南這場大排長龍,人很多時誰要等你一本本蓋章又呼它乾,人少得可憐,那印章的起起落落會太費周章,飆戲才需要去搶戲,戲台一冷清,台上台下盼的都是落幕。
刻下一枚「不食人間煙火」印章,李叔同消泯,世上有了弘一法師,我手裡的印章讓我不禁輕輕一笑,怎麼會無聊得這麼究竟,我曾是怎樣的人,我消失了多少?
夢囈、呢喃、空話、隨口、迴遶、無解、自困,後來我總是很快就能聽出別人話語的屬性,迅速判斷能信不能信以及該信幾分,或決定再聽下去第幾次就是在浪費生命。春夏之際,為了滿枝頭紅麴碗般盛開,落在綠茵的草地有如大朵印花的木棉花,而在樹下主辦下午茶這件事,在我生命中曾起過怎樣的力量,我真的還想不出答案,但我確信,我是因為曾經很浪漫,所以才很懂什麼是無聊。
要兩端都站過才夠,沒經過極致的繁華不能安然於最深沉的寂靜,弘一法師以自身示現,《紅樓夢》是賈府也是曹雪芹自己榮與枯的兩造歷程,我這學期最後一堂文學課有個小主題叫「幸福的侷限」,很多年前我文學課上的是「什麼叫幸福」。
生與滅,夢與覺、真與幻、窮與達、苦與樂、生與死、常與變都是兩端,而生命很奇妙,真切經歷過二元對立,才比較能回歸那本然的一。我是這樣小小站立過兩端後才真正讀懂〈赤壁賦〉裡的水與月,生命的本質與現象,薄霧輕輕貼著水面,空靈低沉的洞簫貼身繞拂,初秋,圓月,人的一生一世與生生世世。
有順有逆而凝睇過生命的實質本體,蘇東坡亮著眼睛對朋友說,一世際遇何足記掛?生命短促何足憂傷?在無止盡的永恆與變異中流轉,我們其實從未真正死去。
白露橫江,水光接天,西元一○七九年,宋神宗元豐二年,七月十六日,一個圓月黃大的靜美夜晚,浪漫撲漫,廣天敻地、無邊無際。
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男子,拿著一本星雲大師著作的《百年佛緣》,守候在佛陀紀念館五和塔外的菩提樹下,迢迢來到佛光山上過年是他許願多年終告成真的美夢,當佛館切菜義工空暇的時間,他就按著書中寫到的每一個景點一一親登履踐,他要跟著大師將佛光山看得仔細,微風吹拂,滿樹菩提葉翻飛,葉背跳閃著朵朵金澤,「或許大師會正巧走過」,他微笑著說,眸子裡跳閃著真摯。
和L一起去採訪二位在大學任教且擔當行政工作的男子,他們因緣際會接辦了弘一法師話劇〈最後的勝利〉,籌辦期間,他們特地請個休假,執意在秋天走一趟杭州虎跑寺,沿循弘一法師當日的足跡,初起上山迷了路,從山頂俯看依稀虎跑寺,然後他們再沿下尋往,就在疑無路擬回頭之處突然一個彎轉,竟就是虎跑泉及李叔同紀念館,從死溯生,尋尋覓覓,他們說,宛如弘一法師有意引領。
臨別送我們至電梯口,他們突然以美聲唱起弘一法師的〈送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多久了,我很難開口唱歌,多遠了,我回不去的大一女生宿舍,那時候,迷漫氤氳熱氣與綠野香波洗髮精清新氣味的水聲嘩啦的浴室,總有人唱有人和,「誰家吹笛畫樓中,斷續聲隨斷續風」,還有那纏綿飆高的「思歸期,憶歸期,往事多少盡在春閨夢裡……」我和L在電梯邊大聲和著他們的忘情浪漫,發現自己將〈送別〉唱得一字不漏,電梯門開,我們唱著走進,門關,他們在門外高聲唱。
浪漫讓我沒錯過任何浪漫,不浪漫後我才真正懂得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