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人在屋簷下躲雨,看到一位禪師撐著傘經過,喊道:「禪師,度我一程吧!」
禪師看他一眼:「你人在屋簷下,不會淋雨,不需要我度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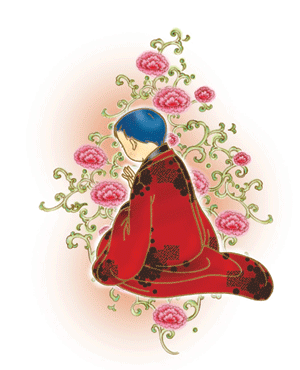 那人走出來,說:「現在我也在雨中,該度我了吧?」
那人走出來,說:「現在我也在雨中,該度我了吧?」
禪師緩緩答道:「我不被雨淋,因為有傘;你被雨淋,因為沒傘。今天是傘度我,你要被度,自己找傘吧!」說完就走了。
我喜歡這則「自傘自度」的公案。我們不也是不識自家寶藏,只一昧東尋西求嗎?何時才能探得訊息呢?
佛陀來此世間,說法四十九年,即是為讓眾生明白並開顯本自具足的真如佛性。在眾多闡揚佛性典籍當中,能貼近生活,直指人心,在敘述上淺顯易懂,讀來令人怦然感動的,當屬《六祖壇經》吧!
《六祖壇經》裡提到「自性」有五十處之多。經文一開頭,惠能大師就開宗明義道:「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既然這清淨無瑕,能解脫一切苦惱,成就佛道的自性佛心,本來存在每個生命裡,為何生命依然殘缺不完美,依然有許多顛簸痛苦?
惠能得法之後,帶著五祖傳給他的衣缽往南行,數百人追過來,第一個趕到的惠明,提掇不動放在石頭上的衣缽,醒悟到傳法信物不能以力爭奪,乃請惠能說法,惠能要他屏息諸緣,勿生一念,然後問他:「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這裡的問號也可改為肯定的驚嘆號。
如同莊子言:「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如同老子言:「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都引來衛道之士的抨擊一般,有不少人見此句也疑惑:如此不思善惡,沒有是非善惡標準,豈不天下大亂?我不禁又想起中央帝王渾沌的故事,渾沌原本天真無邪,被南海王、北海王開了七竅,懂得分辨男女、美醜、大小、好壞……之後,就鬱抑而死了。
只因我們見色緣色,見聲緣聲,有這種種分別,才須世間的尺度、法律,不是嗎?不存善惡之念,不見善惡之相,如風來疏竹,雁過寒潭,任何聲影皆不住,還怕見不到清明的本來面目嗎!
但是,惠能大師可不是叫我們絕思斷念。我們每天一睜開眼,腦筋就不停的運轉(有時連夜晚夢裡亦不得閒),眼見耳聞皆是追逐、攀緣,把自己的身心搞得烏煙瘴氣。等識得佛門心法,或者本身覺照心強者,哪天緊急剎車,開始自覺內觀;此時,又往往矯枉過正了。
記得剛學佛時非常精進。一本《佛門必備課誦》,從「楞嚴咒」、「大悲十小咒」到「普門品」、「阿彌陀經」、「八十八佛大懺悔文」……幾乎背得滾瓜爛熟。每天起個大早,做了傳統寺院的早課,才去上班,晚上下了班,回到家裡,盥洗好,又跪在佛前做晚課。
當時也不甚明了經義,只覺自己業障深重,非佛力無以滅罪。經中所言無常、苦、空之真理,印證於真實人間,誠然不虛,更將我攝受得服服貼貼。幾年下來,抖落眉間愁蹙,外人看到的是一張安詳平和的臉龐。
又過幾年,心中的貪瞋痴如「東風解凍,蟄蟲始振」,又蠢蠢然在血液裡竄囓。雖不似法達法師因誦《法華經》三千部,心生我慢,禮拜六祖而頭不至地,但也和他一樣,只是空誦循聲,未曾達法,徒被經轉。
磨磚不能成鏡,打坐豈能成佛?後來發覺,蒲團上妄念紛飛,只虛耗時間;眼觀鼻、鼻觀心,心如止水,也不一定能見性。
有人將修行與生活硬生生劃分為二,執著「住心看淨」,到後來「猶如木人看花鳥」,成了個凡事不關心,在人間行走卻冷冰冰的木頭人。人生許多時刻,走到這種「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境地,初時,或有孓然清高的喜悅,但又不免有著格格不入,「過盡千帆皆不是」的孤獨寂寞吧。
《六祖壇經》讓人驀然回首,原來「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也是看了《六祖壇經》才體悟為什麼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若無世間的生老病死、成住壞空、悲歡順逆之現象,如何說明緣起、無常之真理?我們又如何將抽象的義理作實際的印證,並從中幡然覺醒,悟出自性?
如何做到「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
一生奉行和弘揚人間佛教的星雲大師,深諳此理,他說見性不難:「生活清貧知足,即見聲聞淡泊之性;明了緣起法則,即見緣覺寧靜之性;度眾不煩不惱,即見菩薩大悲之性;無住無相無念,即見如來不動之性。」說得多好,這淡泊、寧靜、大悲、不動之性,存在心底,卻是從生活、磨練、度眾中顯現出來。
所以,〈行由品〉裡惠能的生平,及求法、得法的歷程,才如此生動,如此親切感人!
佛性本來存在,卻須因緣具足方得成就。惠能送柴到旅店,聞客誦《金剛經》是第一個助緣;安道誠贈十兩銀子,讓他安頓母親,無後顧之憂,是第二個助緣。弘忍大師的「慧眼識英雄」,當然是最大關鍵,印宗法師尊法敬法,為惠能剃髮,再反過來事其為師的大氣度,也非常人可比擬。
「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寶珠在自家懷裡,塵盡則光生,拂塵的手在哪兒?我想迷悟之間的橋樑,是自己累劫的修持功夫,也是一世一世在生活中積聚的福德因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