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新開一門課「文學與傳播」,希望從傳播觀點重新詮釋文學活動,讓中文系學生打開一個較為寬闊的視野。為了使學生很快進入我的訴求重點,我在開場之後即針對〈文學活動結構的宏觀解釋〉展開說明。你引莒哈絲論寫作談「觸知」,引出創作主體的「反思」之必要的問題,其實是整個脈絡的一個環節,我想藉此談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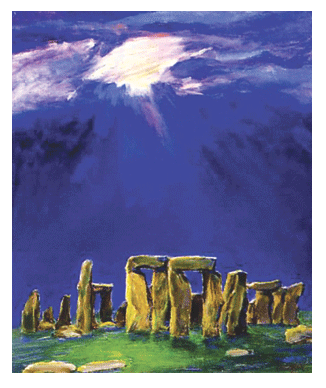 這裡所謂「文學活動」是一個廣義的說法,包括作者的「創作活動」、創作文本的流通過程、讀者的「閱讀活動」以及與文學有關的社會性活動等等;而我要教的,表面上只針對「通路」,但從傳播學所談的傳播模式來分析文學的傳播,也不能不談創作意圖,即作者所欲傳達的那個「為文之用心」,它構成「訊息」的主體內容,至於如何寫作的問題,我倒是不準備詳談,重點擺在文字文本如何通過紙本製作,有效進入流通過程,讓讀者得以取得而展開閱讀,這個部分我把它放在「媒介」的活動結構裡來談,是一個可以建構的大學問,過去比較多的是經驗之談,現在已有許多學理性的分析,相關的研究都正積極展開當中。
這裡所謂「文學活動」是一個廣義的說法,包括作者的「創作活動」、創作文本的流通過程、讀者的「閱讀活動」以及與文學有關的社會性活動等等;而我要教的,表面上只針對「通路」,但從傳播學所談的傳播模式來分析文學的傳播,也不能不談創作意圖,即作者所欲傳達的那個「為文之用心」,它構成「訊息」的主體內容,至於如何寫作的問題,我倒是不準備詳談,重點擺在文字文本如何通過紙本製作,有效進入流通過程,讓讀者得以取得而展開閱讀,這個部分我把它放在「媒介」的活動結構裡來談,是一個可以建構的大學問,過去比較多的是經驗之談,現在已有許多學理性的分析,相關的研究都正積極展開當中。
進一步當然是文本的閱讀,不能不談讀者如何取得?以及如何閱讀?傳播學告訴我們,讀者是不確定的多數,各自有其性情、人生體驗以及人文之教養,作為一個「受播者」,他的「解碼」能力如何?傳播效果如何?等等,在整個文學活動中,這個環節很重要,卻也非常不容易梳理分析,但傳播學提供我們一些和文藝學不一樣的研究取逕,最起碼可以用問卷調查或深度訪談等方式,取得可資論證的材料。
這還不包括媒介轉換或再傳播,譬如詩改編成歌曲來演唱、詩的視覺化、小說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等所牽涉的技術及產業經營問題,甚至不同語言或文化領域的轉譯,也是整體的一環。
思考文學的寫作,如果有這樣的整體觀察,應該能更有比較好的自我定位。回到寫作的本質來看,基本上那也是一種行為表現,「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這種由內而外的過程,可以非常私秘,也可以極其社會化,但不管怎樣,「出以至誠」應該是一個通則,至於言如何發?誠如何出?凡寫作之人,都得有這方面的自覺,你提到的「觸知」與「反思」等,都是這個層次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