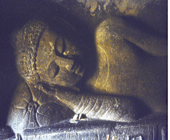 雖然中國政府藉著依法追回或購回或呼籲收藏捐贈等途徑想取回敦煌文物,可是,有多少希望呢?至今仍漂泊於海外的敦煌文物,何時可以回到中國的懷抱,沒有人知道!
雖然中國政府藉著依法追回或購回或呼籲收藏捐贈等途徑想取回敦煌文物,可是,有多少希望呢?至今仍漂泊於海外的敦煌文物,何時可以回到中國的懷抱,沒有人知道!
1
已經有三個多月沒有下雨了,乾旱的大地長不出稻苗來,農作物在烈日下一吋一吋枯黃,龜裂的大地上除了牲畜奄奄一息之外,許多村民們也感覺到似乎末日已經來臨了。
道士陸續進駐旱區祈雨,可是,烏雲短暫聚集之後,有突然散了開來,雨水似乎一直沒有落下來。為了生存,年幼無依,身材瘦小的王圓籙尾隨著逃難的人群,離開了縣城,一路上所見的盡是枯槁的大地,只要可以生食的綠色植物,都被摘光了,樹皮也被逃難的人群剝光了。
印象中,北方的河雖然常年乾枯,但總還有些積水和雜草,遺憾的是,當逃難的人群蜂擁而至時,卻沒有一滴水,河床露出光禿的河床和錯亂的小卵石。個子矮小而顯得瘦弱的道士此刻顯得更加憔悴,一向話就不太多的個性,此刻也沉默了許多!
2
熾熱的陽光下,熙熙攘攘的人潮讓道士心情輕鬆了許多,蹣跚的駱駝與馬匹在敦煌城街巷中走過,濺起些許慵懶的塵埃,人群不緊不慢的走著,沒有人會對身材矮小的道士多看一眼。
當時的敦煌城,人口不多,也看不到昔日往來於絲路的人潮了。街道兩邊住宅仍然古樸,色調也多是戈壁色或者沙漠色的灰黃。
太陽還未升起,大地似乎還在沉睡,道士就起床了,漫步走在四周靜寂的街上。爬上了低矮的城牆看到稍遠處的鳴沙山,沙丘的輪廓如刀鋒樣的流動著;在通往西千佛洞的路上,陸續出現了烽火台,道路兩旁的戈壁沙海中,不時可以見到用黃土與樹枝、草杆摻和劣土構築而成的土墩。此時,敦煌的天空出現了陣陣強風,一望無際的漠野,更顯得淒涼而孤寂。
道士王圓籙來到了鳴沙山發現了埋沒在沙塵中的石窟群,於是,把其中一個石窟打掃乾淨後,帶著簡單的行李住了進去。
有一天,在一個石窟中清掃浮塵時,偶然間在北面的洞壁上發現有一處地方比四周更加突出,於是,找來了一根木棍將突出處的泥土搗下來,卻發現這一處壁面發出異樣的聲響,於是,以更粗的木棍朝那個地方用力敲擊,壁面敲破,出現了一個洞穴,道士向裡面瞄了一眼,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
於是,找了一把鐵鍬,把洞口的泥土都挖開,還是看不清洞內到底有些什麼東西,低著頭,回到自己的洞窟,點燃了蠟燭,借著燭光再朝洞中張望,洞裡堆滿了各式各樣,不同年代的經卷,道士王圓籙突然被眼前的景象嚇住了,驚魂未定之餘,興奮徒步行走了五十里趕往縣城,面見敦煌縣令時,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
縣令認為那兩張紙只不過是廢紙而已,露出冷冷的笑顏。
道士只有失望地走回洞窟。
消息傳出後,道士擔心經卷被人奪取,將一部分密藏於其他洞窟,開始出售。之後,陸續有人以銀元換取文物。
英國探險隊員來過敦煌,以連哄帶騙與利誘的伎倆,讓道士打開了洞窟,在捐一筆功德錢為籌碼後,他暫時住了下來,利用七天七夜的機會打包,裝滿了二十九箱的經卷運回英國倫敦。
法國人來過敦煌,以明買暗奪的手法向王圓籙出價,以每捆十五兩銀子,從中精挑細選了六千多件文物,偷偷拍攝莫高窟全部壁畫帶回法國出版。
日本人也藉探險之名來到了敦煌,取走了五百多件文物。
當清朝官員知道那些不再是無用的廢紙時,第一批送往京城的洞窟文獻從敦煌出發了。沒裝木箱,只用蓆子亂捆,沿途官員伸手進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兒歇腳又得留下幾捆,結果,到京城時已零零落落。運京途中,經不起官商搶劫,抵達北京時,珍貴的經卷已所剩無幾。為了掩飾經卷的遺失或被盜,官員們還無恥地將一份經卷拆成好幾份充數量………
3
走過五千年的歷史,曾經是塞種、月氏、烏孫、匈奴等民族活躍的舞台,位於河西走廊上的敦煌,竟然讓遠行的記憶沉甸了起來。
當年,無論西漢的張騫、東漢的班超,漢代的絲綢之路都是從長安出發,一路向西延伸到敦煌,至少分開南北兩條路,北道出玉門關,南道出陽關,通往西域各國。路,似乎被黃沙淹沒了,可是,曾經擁有的風華卻一直流傳下來。
走過西北大漠戈壁裡的敦煌,莫高窟也只能默默無聞沉睡於三危山麓,沒有太多人關懷的眸光,連願意提起它名字的人也逐漸少了。雖然中國政府藉著依法追回或購回或呼籲收藏捐贈等途徑想取回敦煌文物,可是,有多少希望呢?至今仍漂泊於海外的敦煌文物,何時可以回到中國的懷抱,沒有人知道!
走過敦煌,心情是沉重的,一如當年西夏入侵敦煌時,敦煌的僧侶為了生存必須逃避戰亂,將佛寺收藏的經卷和文書集中起來,祕密藏在洞中,之後,把洞門密封並在上面繪了壁畫,希望能避開西夏國官兵的注意的僧侶們的心情,希望能夠回來。
然而,僧侶們遠走他鄉後,卻一直沒有回來!
恍惚中,自己就是昔日那位無知的道士而非匆忙離去的僧侶,心情始終快樂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