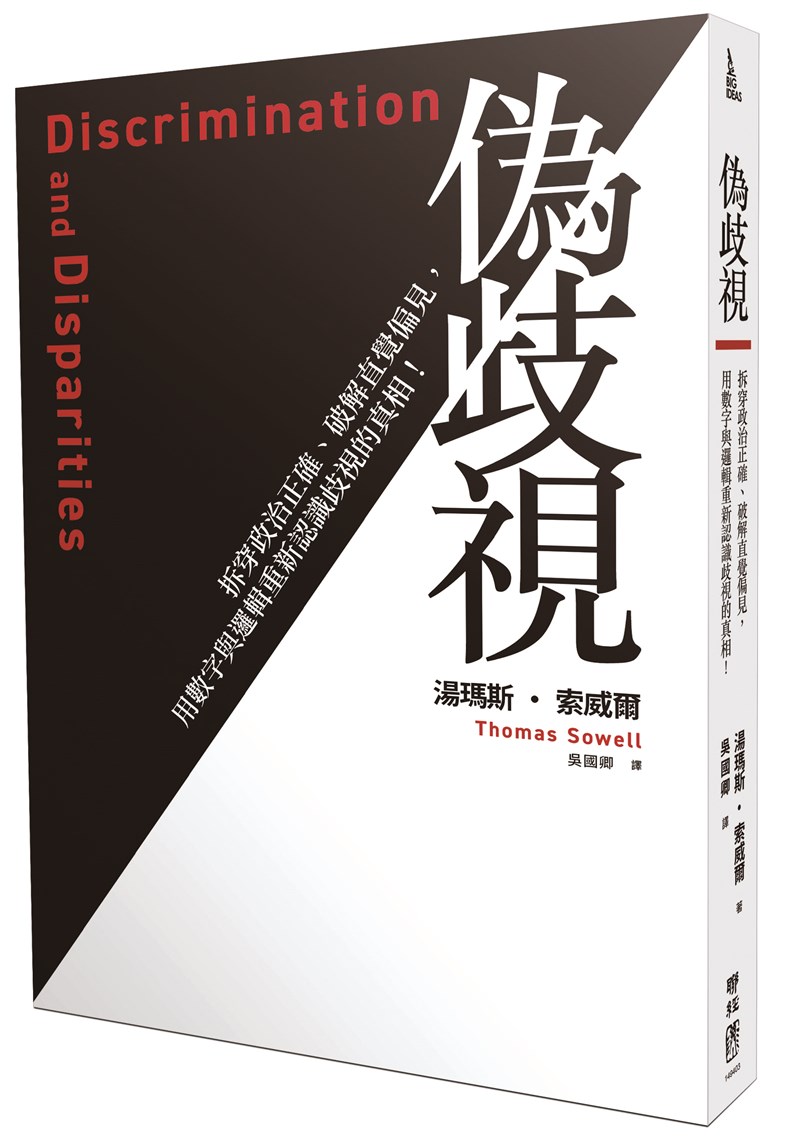 《偽歧視:拆穿政治正確、破解直覺偏見,用數字與邏輯重新認識歧視的真相!》
圖/聯經出版提供
《偽歧視:拆穿政治正確、破解直覺偏見,用數字與邏輯重新認識歧視的真相!》
圖/聯經出版提供
文/湯瑪斯‧索威爾
文字公開宣稱的事,可以用經驗證據來檢驗,但文字影射的東西可能規避防衛。即使一個聽來無辜的詞句,如「所得重分配」不斷重複後,可能暗示有一個我們可以把所得聚集起來,然後將之分配的程序,就像有人可以分配餐桌上的食物或耶誕節的禮物一樣。
在現實中,只有一個比喻式的所得「分配」(distribution,或稱為分布),正如從統計的意義來看,人的身高呈現一個分布,從學步小孩的身高到職業籃球球員超過213公分的身高。但沒有人想像身高的存在,好像獨立的實體,然後真的「被分配」給個人。
就清楚直接的意思來說,大多數所得完全不是被分配而來的,不管是透過正義或不正義的方法。在市場經濟的大多數所得,是藉由提供其他人想要的東西直接賺得的,不管他們是藉著提供勞力、住宅或鑽石賺錢都是如此,但大多數人不會問這個問題,特別是主張所得重分配的人。
暗示不平等的對待
經濟學家史提格里茲等人談到「頂層1%的人攫取的所得比率」;或者像一篇《紐約時報》社論提到頂層1%「聚斂愈來愈高比率的國家財富」。類似的,歐巴馬總統說:「頂層10%的人不再只是獲得我們所得的三分之一,現在他們獲得了半數。」這類表達不是美國的專利,例如,一位牛津教授反覆談到頂層1%的所得是「取自」假想既有的集體「國家所得」。
在這些例子中,關鍵的伎倆是口語上把個人創造的財富集體化,然後描繪那些創造較多財富並因此獲得回報的人,是剝奪其他人應得分額的人。
有時候這些文字伎倆被應用於國際規模之上。在美國由美國人創造的財富被扭曲成「世界財富」的一部分,被美國人不公平地攫取了大部分。但美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一樣,基本上消費的是他們自己製造的東西。美國人從其他國家進口的東西是其他國家出口的東西,用來交換部分美國製造的東西。但在文字的世界裡,所得差異暗示了有人受到其他人的不公平對待。
這類口語的手法——影射而非辯論——可能有助於重分配的目標,但如果不是原本就分配而得的所得或財富,而是直接來自販售有價值的東西,那就不能被重分配。這類口語手法所宣揚的,不是單純的不同類別的所得或財富結果,而是一套從根本上不同的程序,用以決定每個人應獲得多少所得或財富。在這個替代的世界中,第三方代理人憑藉政府的權力,可以凌駕數千萬人對購買的無數產品和服務的定價,而以代理人隨興的想法取代之。
巧妙迴避原有事實
委婉語是另一種形式的影射,可讓想法繞越事實測試或分析測試。當羅爾斯(John Rawls)在他寫的《正義理論》(A Theory of Justice)反覆談到「社會」可以「安排」(arrange)的結果時,這些委婉語巧妙迴避了只有政府有權力推翻數千萬人同意的交易條件這個事實。
羅爾斯不是唯一規避強制的現實的所得重分配主義者,換句話說,當經濟結果不平等,被一個更加危險的權力不平等加劇所取代時,數千萬人喪失自己決定如何過生活的自由。即使是經濟結果不平等,仍容許較不幸者的生活水準提升,但權力原本就是相對的,因此,讓一些人擁有更多權力,意味其他人擁有較少的自由。
隱瞞這個關鍵的利弊交換,導致許多知識分子定義擴張政府權力的好處是得到「新自由」,一如威爾遜的形容。後世的知識分子持續改變自由的歷史定義,把擴張政府規模和權力的假想好處也包括在其中。
(本文摘自聯經出版《偽歧視:拆穿政治正確、破解直覺偏見,用數字與邏輯重新認識歧視的真相!》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