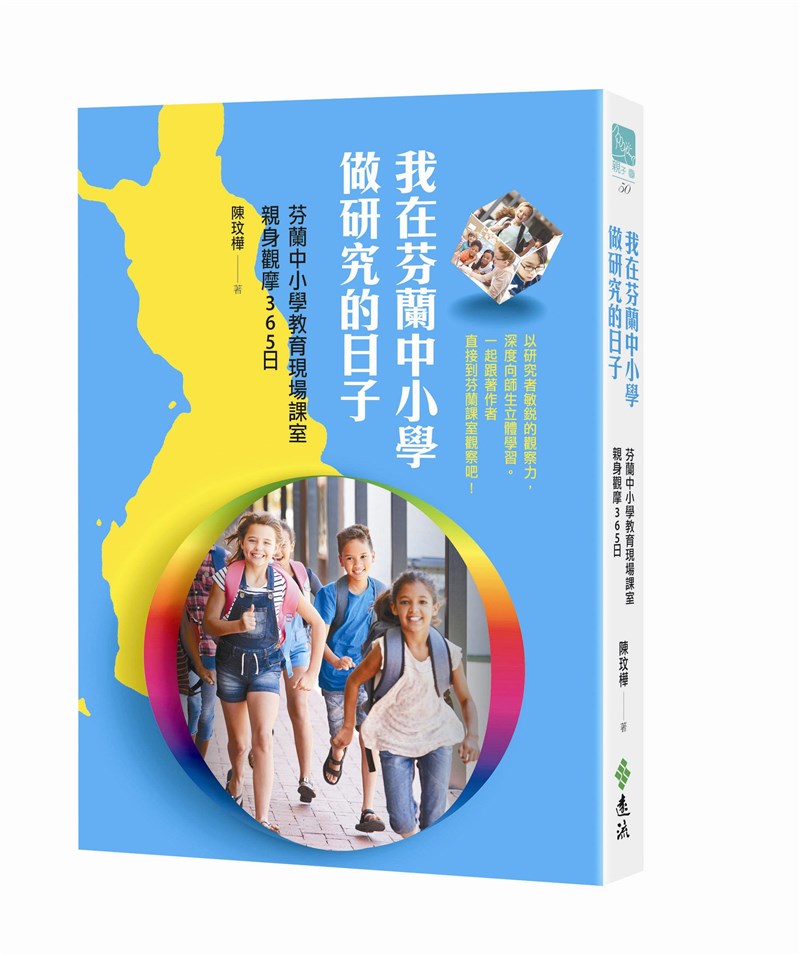 近幾年來,芬蘭的國民教育成為世界各國取經的對象,擔任國中數學教師十多年的陳玟樺遠赴芬蘭,探索他們的教育模式,並將研究寫成博士論文,日前這本論文以《我在芬蘭中小學做研究的日子》為書名出版,本文摘錄其中關於「課間活動」一節精華。
圖/遠流出版提供
近幾年來,芬蘭的國民教育成為世界各國取經的對象,擔任國中數學教師十多年的陳玟樺遠赴芬蘭,探索他們的教育模式,並將研究寫成博士論文,日前這本論文以《我在芬蘭中小學做研究的日子》為書名出版,本文摘錄其中關於「課間活動」一節精華。
圖/遠流出版提供
 學生下課時間在院子遊戲。
圖/陳玟樺提供
學生下課時間在院子遊戲。
圖/陳玟樺提供
文/陳玟樺
芬蘭學校鼓勵孩子戶外遊戲不分四季,這讓學生的身體發展可以獲得持續且均衡,有助於回到教室後學習專注力集中,至於成人的側身照護則是配套作法,如師長們的輪流導護便是一例。當然,根據教學現場的長期觀察與訪談,我以為,此配套也有賴於第一線教師對政策的盡力落實,讓政策與實務之間的連結能有效接軌,然而,我也不禁為教師們感到憂心是——長期擔任導護工作的老師們要利用什麼時間休息?那「飛奔式」走法是否同時也蘊含有相當壓力?芬蘭教師們的情緒地景又是如何呢……
校長的苦口婆心
每周三的午後兩點到四點,為個案學校全體教師的共同備課,此日,學生會陸續在兩點前便放學完畢,教師則會齊聚於學校咖啡廳進行會議。
最近,校長在每周會議上不斷地強調擔任課間導護的教師應在課堂結束後「盡快」抵達院子以為孩子的遊戲安全進行照護與把關(這馬上讓我聯想到英文老師「飛奔式」走法),「這是學校任務的一部分,我們必須要準時抵達……」、「這是為了孩子們的安全,安全第一,請大家務必配合……」校長臉色有些沉重地說。
今日會議明顯結束較晚,才一解散,老師們幾乎都急著到衣帽間整裝更鞋、匆忙下班。「準時下班」是芬蘭社會的顯著文化,很多老師都趕著要去學校接回孩子,少數一些則是去參加社團或社交活動。
「可能我們做得還不夠好,也可能是有些老師因事耽擱了……」英文老師一邊戴上毛帽一邊與我分享她今日的會後心得。
「因事耽擱?」我疑惑地問。
「沒有人會不關心孩子的安全,你可以說芬蘭人是全世界上最重視孩子福利和安全的國家之一……老師一定是因為什麼事情被耽擱了才會沒有準時去院子擔任導護……」英文老師似乎有些同理地回答。
「剛剛聽校長談起,似乎並非所有的老師都擔任導護,是這樣嗎?」我問英文老師。「是啊,已有其他任務的老師便不會在名單上面。」英文老師接著說,「像音樂老師……她在每一節下課後可能會需要去檢查樂器使用後的狀態,相信我,這不會比擔任導護輕鬆的……」她換上雪靴後又套上厚重外套,動作熟練且看似輕而易舉。
「對了,K,明天我們有訪談,一樣在咖啡廳見嗎?」在她預備離去前,我趕緊提醒她明天和她的約會。
「啊,我忘了告訴你……那時段我正好被排到要督導……如果你不介意,明天可以直接約在院子裡見面,當然,我們也可以再約時間。」英文老師臨走前這麼說。
事實上,不僅英文老師,這個冬天,不少老師都和我約在院子做訪談,談話中常伴隨雪花紛飛,怕冷如我在初抵芬蘭時常無法專心聽說。不過,也因為如此,我有機會近距離且長期地觀察到孩子們在大雪紛飛時依然活力飽滿、活蹦亂跳。他們穿著厚重雪衣、雪靴、吊帶褲……穿梭追逐,顯然無礙於這零下十幾度的近身包圍,移動仍十分靈活,即使追逐中跌跤常見,卻也絲毫興致未減。
強制到戶外遊戲
「這麼冷的天氣孩子們卻總是玩得這麼開心。」我對身邊擔任督導的英文老師說。
「是啊!他們課間一定要出來玩一玩,」她接著說:「這是芬蘭學校教育的特色——強制到院子遊戲。」
「強制?強制他們一定要出來戶外遊戲嗎?」雖然已閱讀過一些文獻,但第一次從教學現場老師口中說出時仍想再探究竟。
「對,他們需要活動才能保有健康身體,一直待在教室反而容易生病、頭痛……」英文老師進一步解釋,「建築物也要休息……」。
以往從媒體文章中得知芬蘭鼓勵學生在遊戲中學習、重視課間活動等,再探討芬蘭《基礎教育法》、二○一六新課綱《基礎教育核心課程》後也發現,關於課間活動也有相關規定。
根據一般性規定,學校在每節至少四十五分鐘的教學時間結束後,要讓學生休息十五分鐘,若上課時間更長(如六十分鐘或七十五分鐘),則休息時間也必須相應延長。然而,在不違反此規定下,當地市政當局和學校仍有很大的自主權可以決定自己的日行程作息,是以,芬蘭沒有統一規定日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