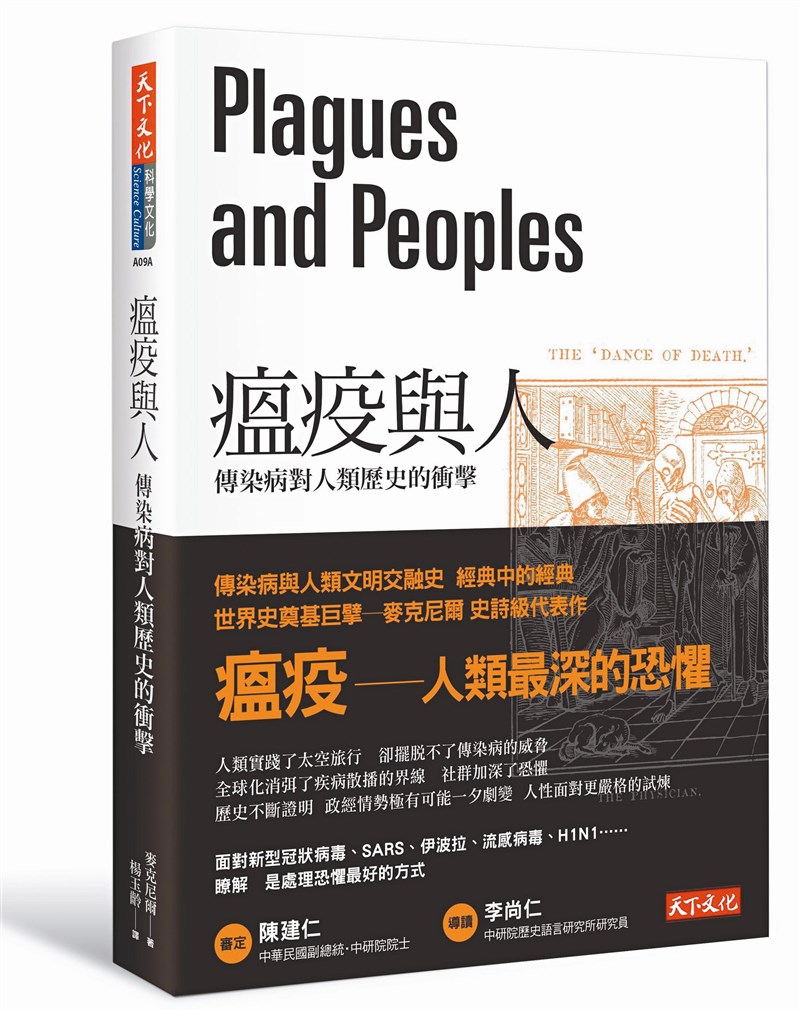 《瘟疫與人》
圖/天下文化提供
《瘟疫與人》
圖/天下文化提供
文/麥克尼爾
由官方組成的國際醫學組織,要回溯到一九○九年。當時,國際公共衛生處在巴黎設立,任務是監管鼠疫、霍亂、天花、斑疹傷寒以及黃熱病的暴發情形。該處同時也試圖為歐洲國家制定統一的衛生及檢疫規章。在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聯盟也設立了一個衛生部。裡頭有許多專責委員會,討論諸如瘧疾、天花、漢生病以及梅毒這類疾病在世界上的發生率。但是在這段期間,更重要的工作則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執行的抗黃熱病,以及抗瘧疾計畫所完成。
然後是一九四八年,更具野心的世界衛生組織成立。擁有來自政府的充分支持,世界衛生組織開始出動,把醫學科技的新知帶到世界上各個落後地區,不論當地政府是否願意合作。
因此,自一九四○年以來,醫藥科技和公共衛生行政,對於人類生活環境所帶來的衝擊,已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在大部分地區,流行病已經變得無足輕重,而且許多流行病在從前流行得很嚴重的地區,也變得很少見了。人類健康與快樂的淨增值,再怎樣形容都不嫌誇大;的確,現在的人,甚至是我們的祖父輩,都需要發揮一下想像力,才能了解傳染病從前對人類的意義。
然而,正如人類學會擅改複雜生態關係的新方法後,可能會出現的後果般,醫藥研究自一八八○年代起對於微寄生所進行的操控,也已經製造出一些始料未及的副作用和新危機。其中一個有趣但也很諷刺的結果,即是產生因太過清潔而引起的疾病。最主要的例子莫過於小兒麻痺在二十世紀崛起,尤其是在最注重衛生習慣細節的階層中。
難纏的感冒病毒
另一類在未來仍對人類有著重要性(至少有此潛力)的流行病,最佳例子莫過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間的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存在的時間已經相當長久了,而且它的流傳之快,引發的免疫期效之短,以及這類病毒的不穩定程度,都非常明顯。
一九一八年後,研究人員經過一世代的研究,建立了三種已知的不同病毒株;而且也有能力創造出對付它們的疫苗。然而,問題沒有這麼簡單,因為流感病毒本身很不穩定,每隔一小段時間,就會改變它的化學結構細節。因此,只要出現任何一波廣泛的新流行,研究人員幾乎都可以肯定,引起這次感冒的病毒其改變程度,必定大到足以逃過去年疫苗在人體血液中製造的抗體。
因此,流感病毒的變化,以及其他傳染病原生物的突變,可能性依然很高。例如,一九五七年時,一場新的「亞洲型」流感病毒在香港出現;但是,它在美國發展到流行病程度之前,對抗這個新病毒的疫苗早已大量製造完成,數量多得足以影響這波流行的發病率和強度。然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公共衛生管理當局具備敏捷的步伐,也需要私人企業毫不遲疑的參與辨識新流感病毒,以及大規模開發並製造疫苗。
第三項可能會發生的糟糕結果,在於為了癱瘓敵國人民而進行的生物戰研究,在散播致命病原生物於敵方時,有可能會為部分地區(或是全世界)釀成流行病大災難。除了這些可以想像的災難之外,很顯然,人類還是必須固守在食物鏈裡限定好的位置上。過去一百五十年來,由於公共衛生策略的成功,造就了人類數目激增,對於糧食供應也造成了壓力。其他肇因於人口增加所產生的壓力,也以各種方式展現出來—不只是流行病學,也包括社會學、心理學甚至政治學。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瘟疫與人》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