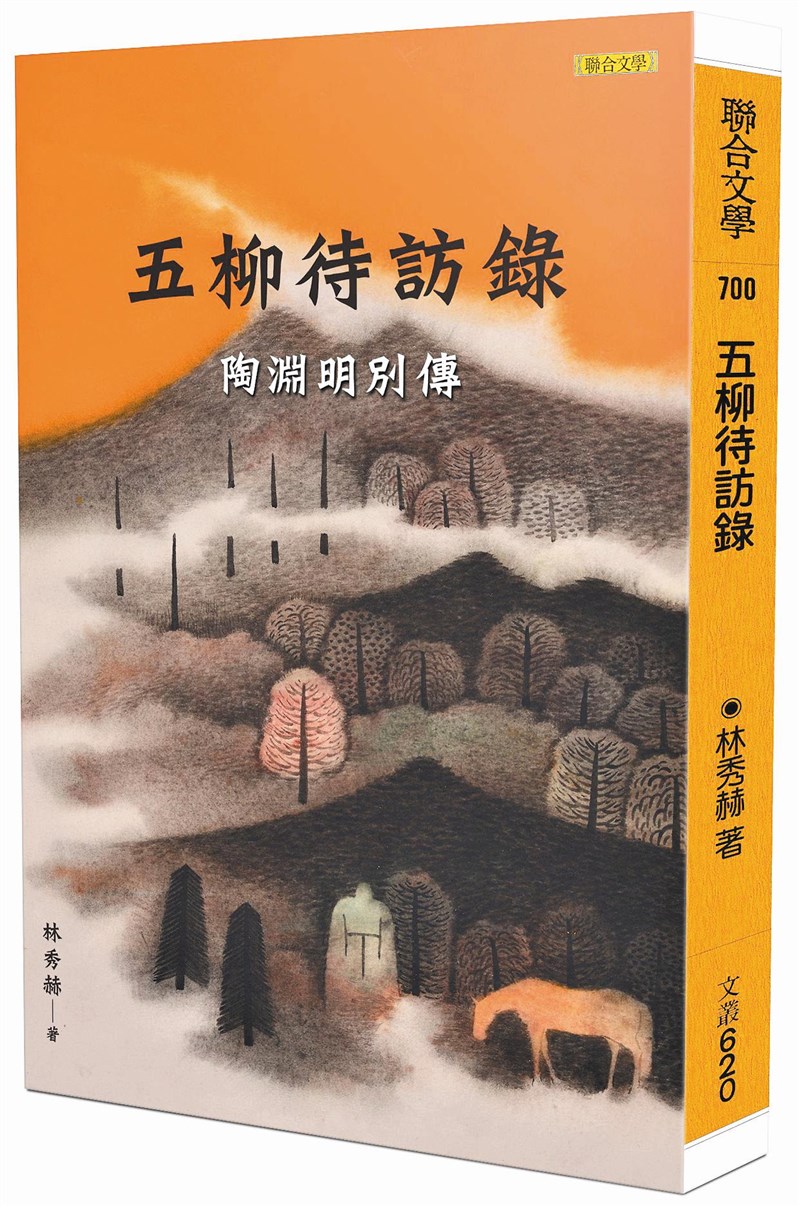 《五柳待訪錄》曾獲2014年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長篇歷史小說獎,被該屆評審小說家何致和譽為:「翻轉歷史,改寫〈桃花源記〉的由來,幾乎找不到任何會折損說服力的破綻。」
《五柳待訪錄》曾獲2014年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長篇歷史小說獎,被該屆評審小說家何致和譽為:「翻轉歷史,改寫〈桃花源記〉的由來,幾乎找不到任何會折損說服力的破綻。」
文╱林秀赫
劉家畢竟是仕宦家族,劉遺民本名劉程之,曾是當地柴桑縣的縣令,儘管之後辭官歸隱,在柴桑一帶仍是極有名望的人物,許多尋陽的望族,也紛紛派人前來關心。所以劉遺民家中探病的客人,往來絡繹不絕,在劉遺民尚未斷氣之前,不知情的人們,還以為劉家是在辦什麼喜事呢。
由於當時的陶淵明同樣病著,那個時候幾位老友,並未把劉遺民重病的消息,給陶家人知道。
可惜劉遺民昏睡的時候,無法見人,偶爾醒來,想見的也只有宗炳和陶淵明。病榻前,五個女兒哭成一團,有的更有願意折壽來延長父親性命。劉遺民見女兒有這等孝心,內心相當難受。他因為夫人生不出男丁,彼此感情不睦。多年潛心向佛的他,相信自己曾於坐定當中三度見過佛祖,常求佛祖能賜給他一子弄璋,但終其一生,還是無法得償所願。他每次到陶家,見到元亮的兒子們,心裡總有說不出的羨慕。
「五個,是五個兒子啊。」
陶淵明知道他的心思,特地在彼此唱和的時候,試著解緩他的心結:
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
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疏。
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他想,元亮對他的勸慰,和慧遠大師給他的指點,是一樣的。但是他始終僵持,任誰的話也聽不進去,直到人之將死才明白陶淵明說的道理。
在他最後要離開的那三天,醒來便氣若游絲地說:
「陶老弟可來看我了?」
「聽說陶彭澤也正病著呢。」
「看來他必定是病得不輕啊,不然又怎會不過來看我呢?」
「老爺不必掛記他,等你病好,便可見到了。」
「我想是很難了。」
最後氣息奄奄的他,雖等到宗炳,但始終等不到陶淵明。
此外,劉家的眷屬也得知陶淵明重病將死的消息,發喪的時候,以為沒有喪家互相弔唁的道理,自然也繞過了陶家。
未料陶淵明竟是活了過來。
轉趨康復的他,在養病期間的某日,見周續之排闥直入,一見到陶淵明便禁不住地哭喊道:「元亮,咱尋陽三隱就此少一人了呀!」
說完就又垂頭喪氣,精神恍惚地走了出去。日後周續之的情性,也有了很大的轉變,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陶淵明這才得知劉遺民的死訊,當下也難過到說不出話來。
他倚在榻上,腦中一片空白,隨後耳際慢慢有了劉老兄談笑的聲音,逐漸擴大成他整個人的身影。老劉在宴席中,穿梭為大家斟酒,好不熱鬧。瞬間這樣的一位老友,竟然比重病的他,早一步走了。他完全無法相信。
他想,程之與我是多麼貼己的好友啊!當年他為柴桑縣令,我為彭澤縣令。我倆同時離開官場,一起在廬山下隱居生活,可是如今我大病痊癒,但程之怎麼就這樣死了呢?
陶淵明想著想著,回憶起更多往日與劉遺民相處之事。他一跛一跛地走到劉家,但是劉夫人不願見他,她與翟氏不同,對丈夫的酒友一向特別厭惡。尤其丈夫還曾以陶家五子,來譏諷她生了五個女兒。
陶淵明向其族人問了劉遺民的墳塚,便走向西林附近一處的劉家土地,見那裡有一坯新的土丘,想來便是劉遺民的歸所。
他把當初壽宴上所寫的〈止酒〉,除了將全詩的「止」字全改為「行」字外,並加入了劉遺民那天寫的「行字句」,於劉遺民的墳前誦唸之後,與金紙一同燒為灰燼。
徒知行不樂,未信行利己。
始覺行為善,今朝真行矣。
從此一行去,將行扶桑涘。
清顏行宿容,奚行千萬祀。
「劉兄,這首詩〈行酒〉也蠻好的不是嗎?」
迎著田野的微風,陶淵明嘆道:「雖然無法見到你最後一面,但是平日相處都已盡興了,見不見最後一面又何妨呢?」
他看著墳前的碑文,其中記有孝男數人的名字。他見了搖頭,劉兄既然膝下無子,刻上女兒的名字也就罷了,何必硬是刻上這些造假的孝男。他為劉遺民的一生感到遺憾,心想若非他執著於男丁,也不會與劉夫人疏離,更以為自己蒙了前世罪孽而唯恐終生不得子,整日在山中禮佛懺悔,不過是再耽誤了與妻女共享天倫的機會罷了。
只是陶淵明沒想到的是,劉遺民墓碑上所刻的數名孝男,是劉遺民的女兒協議刻上的。這些真實的名字、虛幻的名字,伴隨著這位尋陽隱士,永遠靜臥於他所隱居的這塊土地。
(摘自《五柳待訪錄:陶淵明別傳》,聯合文學出版)
作者簡介
林秀赫
1982年冬天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博士,從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林秀赫的小說議題嚴肅,擅長發掘深刻的社會問題,洞悉人類存在的荒謬,對於批判體制有極深的力道。2015年首部小說《嬰兒整形》結合科技、美學與當代思潮,探索倫理與主體性議題,獲得吳濁流文學獎長篇小說首獎肯定,為該獎歷年最年輕得主。第二部小說《老人革命》以幽默諷刺的筆法,批判當今社會對老人的歧視,描寫一群保衛投注站的老人重新找回尊嚴的過程,所改編的電影劇本榮獲2016年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項目創投」最佳創意獎、MPA亞太合作特別獎、坎城新影人基金大獎。
本書《五柳待訪錄》曾獲2014年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長篇歷史小說獎,被該屆評審小說家何致和譽為:「翻轉歷史,改寫〈桃花源記〉的由來,幾乎找不到任何會折損說服力的破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