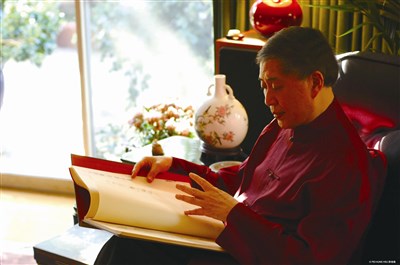 攝影/許培鴻
攝影/許培鴻
中國傳統文化有幾千年的歷史,
如何將這個古老傳統拉進二十一世紀,
讓它在現代舞台上重新獲得一個新的意義、新的詮釋?
講者/白先勇 文與圖/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提供
我在異國教書,離開了中國文學文化的崗位,因而能慢慢對中國文化做一些反省。到了外國,會產生一種比較視野,使我們得以進行各別比較。看看別人的文學和文化是怎樣,再回過頭看看自己的文學和文化,就會獲得新的看法、新的體驗和新的感受,並感覺更加親近。
我在臺大外文系時常常到中文系聽課,去聽葉嘉瑩老師、鄭騫老師和臺靜農老師的古典詩詞課程,還有王叔岷老師的《莊子》。可見我那時已不自覺地在做這個工作,希望能融合西方文化傳統與中國文化傳統,使它變成我們自己的文學創作,而我覺得自己很適合做這件事。
西方文學給我很多啟發,尤其是現代主義的求新精神,與對二十世紀的感性思考,使得他們的寫作形式有了新的表現方式。西方所謂的現代運動,和繪畫、音樂、表演藝術、舞台藝術及電影都是一體相關的;這些思維對當時的我來說都有影響。我也常看新潮電影,法國和義大利的都看,我們接受了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化,接觸了這些文學、藝術及電影,吸收了他們的形式之後,再回歸到創作。
在題材、感性和人生觀方面,我則受到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傳統影響很深。我在國外時,對這方面慢慢有些想法與省思。也同時在想應該如何將這兩個傳統結合起來。中國傳統文化有幾千年的歷史,如何將這個古老傳統拉進二十一世紀,讓它在現代舞台上重新獲得一個新的意義、新的詮釋,我們需要做一個工作,就是將自己的文化放進世界裡頭,跟其他文化、西方文化進行比較,思考如何給予它一個定位。
我這些年來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不論是寫小說,或是將小說《遊園驚夢》改成舞台劇,都是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後來我做崑曲,是接續這個思路而來,這個思路就是:如何將古老傳統放在現代舞台上。現在是二十一世紀,現代舞台完全客觀的環境都變調了,如何將傳統文化放在上面且讓它持續發光呢?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也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挑戰。
其實我們從十九世紀以來一直在做,十九世紀西方強勢的文化進來以後,中國文化首次面臨一個更強勢、更優越的文化入侵,幾乎打散了傳統文化的結構,所以二十世紀以降,我們不斷重新建構、追趕現代思想,以期在追求現代化之際,亦不失作為中華民族的身分認同,這是讓我們最苦惱、最具挑戰性之處。
學思經驗分享
˙我們都有一種「求新望變」的想法。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我們是在重新建設人生的價值,而辦雜誌就是在履行這個工作,文學對我們來說無比神聖,是安身立命的所在。
˙我認為要成為一位作家,要有天生的寫作和創作細胞,後續的發展才是可以鍛鍊的部分;先有了傾向和文才,再給你一條發展的道路,才能成為作家。
˙寫作需要自我要求,即如何以最合適的方法將這篇小說呈現出來。夏濟安先生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教訓,他說:「文學的高下不在於你寫什麼,最重要的是你怎麼寫。」
˙到了外國,會產生一種比較視野,使我們得以進行各別比較。看看別人的文學和文化是怎樣,再回過頭看看自己的文學和文化,就會獲得新的看法、新的體驗和新的感受,並感覺更加親近。�(摘自《我的學思歷程7》)
作者簡介
白先勇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學士、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曾長期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聖芭芭拉校區,亦是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訪問學者和崑曲青春版《牡丹亭》製作人。著有短篇小說集《遊園驚夢》、《臺北人》、《寂寞的十七歲》、《紐約客》;散文集《驀然回首》、《樹猶如此》;長篇小說《孽子》等。曾創辦《現代文學》,並獲頒國家文藝獎、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博士等殊榮。今以崑曲義工自許,大力推廣美學典範《牡丹亭》,為華人續一曲婉轉老調,重振傳統文化的優雅風采,喚起華人心中共同的青春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