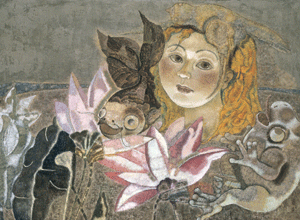
托爾斯泰的眼睛———悲憫
托爾斯泰獻給人類的主要精神財富,就是這充滿普世之愛的悲憫目光,包括不以惡抗惡學說在內的他全部著作只是這種偉大目光的解說詞。
一般說來,一個作家所體驗到的人類苦難,總是以他個人的坎坷經歷和艱苦磨難作為底子並從中昇華起來的。感受了自己的苦難才能同情別人的苦難,體驗了自己面對苦難的弱點才能憐憫別人的弱點。托爾斯泰卻不是這樣。這位伯爵先生在人生道路上是如何養尊處優、平步青雲是大多數讀者都心中有數的。所以,托爾斯泰的苦難意識和悲憫心腸初初看上去總覺得有點虛假。
一個沒有被現實的苦難深深傷害過的人可以當偉大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心理學家而不會成為作家,因為即使一位平庸的作家也是由造化的捉弄和折磨造就的,一位偉大作家幾乎非得以心靈的巨大傷害和嚴重殘缺為代價不可。高爾基說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唯一健全的心靈,等於說托爾斯泰是唯一沒有資格當作家的人。
托爾斯泰天生具有聖徒的稟賦,他動筆之初就是以聖徒的身分寫作的。《盧塞恩》、《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爾》、《五月的塞瓦斯托波爾》作為小說只能說是平庸之作,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處女作《窮人》的輝煌才華有天壤之別,可是在精神上他們卻完全相通。托爾斯泰被人類社會的苦難和存在論意義上的苦難深深傷害,為人類尋找出路的熱腸折磨得他寢食不安。他一面對生命意義作形而上的思考,一面牽掛著每一個農奴的切身貧困與病痛。
他知道沒有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解除我們所面對的困境,這種深重的絕望使得「唯一健全的心靈」變得千瘡百孔。「托爾斯泰主義」是他獻給人類的虔誠祈禱,他對祈禱的效果非常缺乏信心。人類只能按照自己的暴力邏輯相互傷害下去,所以他用那麼悲憫的眼光久久凝視著人類。
像一切偉大的心靈一樣,托爾斯泰時時為人類的苦難而憂傷。
索忍尼辛的眼睛———對抗
當文壇盟主高爾基帶領著一批禦用文人歌頌政治犯們開鑿的白海運河時,索忍尼辛只能在心裡默默地抗議。高爾基從中看見了勞動的歡樂,索忍尼辛卻從中發現了奴役和傷害。
紅軍軍官和數學教師出身的勞改犯人索忍尼辛,與現實世界的關係長期保持著高度緊張。這不但說明了政治迫害的持久性,更說明了他在精神上一直堅貞不屈。他的炯炯目光不但表現出勢不兩立的對抗意志,還表現出發現者的非凡洞察力,同時還有與罪惡力量牢牢對視看看究竟誰比誰更能博得未來之認可的決絕態度。
索忍尼辛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紀,他可能只是一個文學讀者而不會成為作家。可是,殘酷的現實總是刺激著他的感情生活,一代一代死難者在天國、在冥府不斷傾訴著冤情和屈辱。為一切冤魂代言的善良願望、為罪惡的歷史留下見證的偉大激情使得這個資質庸常的人成為了一個時代的良知。他的文本雖然缺乏精神超越性,可是他讓死去的靈魂和活著的靈魂都得到了安慰。
索忍尼辛是一切屈辱靈魂的撫慰者。在文學上,他繼承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高爾基注重社會問題的傳統,可是,比所有前輩更加深重的苦難使他不得不成為文學的叛徒,《古拉格群島》對文學規範的放棄和破壞使得索忍尼辛成為了聖徒型作家。此前,在俄羅斯文學史上只有杜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少數幾個人才當得起這樣的偉大稱號。
有的作家的使命是創造文學精品,比如契訶夫、霍桑、海明威,有的作家的使命是引進非文學因素使文學的概念得到拓展,比如這個索忍尼辛。
讓我驚訝不已的事情還有,從索忍尼辛的照片不難看出,這個長期囚禁在地獄中的人已經染上了地獄色彩的神經質,可是,他的文體卻一直那麼從容、純正。無論是他的政論《莫要靠謊言過日子》,還是他的小說《癌病房》,還是歷史報告體的《古拉格群島》,都沒有喪心病狂、歇斯底里的風格和氣息。我將此看作他心靈偉大的見證。
盧梭的眼睛———善良
與其說盧梭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不如說他是一個「天真主義」者。他對人類美德的信任與禮贊不但天真而且淺薄。他終生都像一個沒有長大的孩子,內心充滿了孩子的單純與善良。
在近代思想家中,對人類精神影響最大的人物有兩個,一個是達爾文,另一個就是盧梭。達爾文的進化學說為人類提供了世界觀(演變的)和歷史觀(進化的),盧梭的契約學說為人類提供了倫理觀(契約的)和價值觀(天賦人權、權利平等)。
作為一個罵罵咧咧的反抗者和批評者,後人難免將盧梭想像為陰鷙而又刻毒的惡魔形象,甚至將他想像為看透世界的虛無主義者。然而,事實與此相反,盧梭不但是一個善良的人,他還是一個淺薄的性善論者。他經歷了那麼多的坎坷與磨難,忍受過那麼多的歧視和淩辱,可是在他的筆下卻找不到一個壞人。他認為人類和社會是壞的,個人卻是好的,有時候個人變壞那是因為受到不合理的社會倫理關係的玷污和摧折。
只有那些內心的善良強大到足夠博得自己信賴的人,才會相信人性中的善良是占主導地位的,才會相信人類可以仰仗自身的美德建立合理的社會秩序和人間幸福。從盧梭的眼神之中,我們可以相信這是一個絕頂善良的人。感謝盧梭同一時代的畫家對他的敏銳的觀察、深刻的理解和準確的描繪,為他留下了如此震撼人心的眼神。在眾蒙時代諸多大師之中,只有盧梭有這樣善良的眼神。
盧梭的性善論主張和道德化傾向都有點像孔子,將自己的主要精力投注於社會倫理的思考和建樹也是他們的共同之處。但他們的價值觀有著某種對立,孔子希望在等級秩序中落實每個個體的身分和位置,盧梭要求以所有個體的平等為前提建立社會秩序。這個源自內心善良的願望彌補了盧梭的天真和淺薄,使得他的思想具有深刻的震撼力和永恒的精神魅力。
魯迅的眼睛———冷漠
魯迅用他的筆告訴我們,人睡到不知道時候的時候,就會有影來告別。
魯迅用這張照片告訴我們,人活到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的時候,就會與人間不辭而別。
一個作家如果不為人類的美德所感動他就成不了作家。一個作家如果不為人類的罪性感到震撼與失望他就成不了有深度的作家。一個作家如果不為人類的永恒苦難悲憫而憂傷他就成不了偉大作家。
魯迅從一開始就是一位有深度的作家。他從少不更事起就被人類的罪性深深傷害,終其一生都在與人類的罪性艱苦搏鬥。最深的傷害常常導致最大的厭倦和冷漠,魯迅說他常常感到自己所住的並非人間,這句話有時候需要反過來說酖酖他常常並非住在人間。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裡,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裡,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裡,我不願去。……我不如彷徨於無地。」(《影的告別》)
他既是一個影,也是一個遊魂。既是「遊魂」,有時候似乎住在人間,有時候一定要遊到人間之外、甚至天堂和地獄之外的。
照片上的這個魯迅,不但遊到了人間之外,甚至遊到了「存在」之外。
一個作家如果從來沒有到人間之外去遊歷過居住過,他如何能夠審視人間的罪性呢?
一個作家如果從來沒有到存在之外去遊歷過居住過,他如何能夠洞穿存在的真相呢?
一個作家如果到人間之外去遊歷過居住過,他怎麼會自陷於人間的得失,而不為人間的生老病死生起悲憫心呢?
一個作家如果到存在之外去遊歷過居住過,他怎麼會自囚於雲煙一般虛幻的榮華富貴,而不為生命的溫熱獻上一絲感傷的微笑呢?
當魯迅回到人間、回到存在之中時,他點著一支香煙,在一群年輕木刻家的簇擁下靜靜地微笑,那是他存在於人間照片上的唯一微笑。
遊歷在存在之外的人是寒冷的。在我的心裡,對於這個被絕望驅趕到存在之外的人總是懷著一絲溫熱的憐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