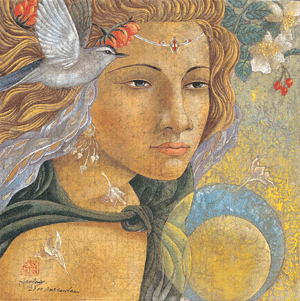
卡夫卡的眼睛—恐懼
世界上最能抓住讀者眼睛的眼睛,無疑是卡夫卡的眼睛。
卡夫卡的眼睛充分宣示了他內心的柔弱和恐懼。也許你會像觸電一般被他喚醒了自己內心同樣的柔弱與恐懼,也許你內心甦醒的是對於一個柔弱而又恐懼的孩子的深深的憐憫與關愛。總之,只要你看見了這樣的眼睛,你就一輩子擺脫不了他對你的傾訴與籲請。
卡夫卡說,作家就是一個弱小的生命。他還說,為了原諒自己內心的弱小,他總是把外部世界描寫得很強大。這個保險公司的小職員一生都害怕父親,好像被他的父親所壓垮。其實他是被存在本身所壓垮。世界和生命都是完全出乎他意料的存在,他被存在的真相嚇得喘不過氣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句話用在卡夫卡身上是再合適不過。
劉青漢說,魯迅筆下的狂人突然發現罪惡的人類「原來如此」,耶穌卻知道罪惡的人類「本來如此」。這個精闢論斷有助於我們理解中西精神文化的差別。可是,西方人並不是簡單地接受耶穌的結論,每一代精神巨人都是重新發現「本來如此」的。在他意識到「本來如此」之前,也驚恐地品嘗過「原來如此」的震撼。
卡夫卡的眼神就是這種發現的驚訝與恐懼。
卡夫卡說他的作品只是他隨手記錄下來的噩夢,他甚至立下遺囑讓朋友把這些文字全部燒掉。他實在不喜歡他所體驗到的存在的柔弱、恐懼與痛苦,他深知「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他每天都在籲請信仰的降臨,因為真正的生活就是信仰本身。
這是一雙最真誠地為信仰而焦慮的眼睛。他好像決心把上帝看個清清楚楚。最後他說:「上帝居住在神秘和黑暗之中。」
當我們相信神秘和黑暗之中居住著上帝的時候,是不是可以減少一點恐懼呢?
普魯斯特的眼睛———夢幻
夢不僅是大腦的一種思維狀態,也是生命的一種存在形式。而文學就是人類的夢幻。所以,所有的文學大師都無法與夢脫盡關系。
世界上有一種病人,醫生永遠看不到患者的臨床表現,因為這種病發生在夜間。誰曾見過夢遊者的身影和眼神呢?可是,自從普魯斯特成為著名作家之後,每個有機會讀到他的照片的人都可以見識夢遊者的眼神和靈魂。
卡夫卡說他的作品就是他的噩夢,這等於說人生就是一場噩夢。普魯斯特好像有不同看法,他拉著卡夫卡的手,帶他來到一座花園樓房,在「格萊高爾一覺醒來變成了一隻大甲蟲」的那張床上,恍恍惚惚地回憶起睡覺前母親慈愛地擁抱他的溫暖感覺。這時奶奶送來了一隻餡餅,普魯斯特還沒有品嘗就感覺到了濃郁的甘甜和馨香,這是對曾經有過的甘甜和馨香的回憶呢,還是在夢中幻想著的甘甜和馨香?
普魯斯特依然拉著卡夫卡的手,迷迷糊糊地來到海邊,欣賞陽光在海浪上跳舞,美麗的舞裙一會兒變成紅色,一會兒變成金色。這時一個送牛奶的村姑款款走來,陽光在她臉上開成了一朵變化不拘的小花。普魯斯特癡迷地讚歎,生活就像陽光一樣,在任何地方都閃爍著詩意。詩人不過是這些詩意的感受器。
誰都知道,普魯斯特因病不能接觸空氣,只能長期封閉在室內。他是一位生活的囚徒,這才是真正的囚徒。
卡夫卡禁不住嘟囔著說,可憐的夢遊者,你都幾十年沒有見過陽光了。
普魯斯特說,我在生活中沒有見過陽光,不見得夢中也沒有陽光。生活不過是夢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噩夢又是生活很小的一部分。何必被那一小部分壓垮呢?
一位詩人說,不要以為我在這裡,就只是在這裡。普魯斯特說,不要以為我活在生活中,就只是在生活中。
人類是病入膏肓的夢遊者,作家是喚醒夢中記憶的通靈師。
文學大師的存在方式就像村姑臉上的陽光之花一樣變化不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睛———疑惑
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一隻眼睛,從額頭到下巴整個臉部就是他的眼睛,額頭則是他的眼珠子。深重的苦難在這隻眼睛裡陰暗地閃爍,嚴重得無以復加的神經質在這隻眼珠子上翻滾顫慄。在他年僅二十四歲的時候,別林斯基就從這位《窮人》作者神經質的敏感與善良中看到了俄羅斯文學的希望,但是這顆希望之星升起得艱難而又緩慢。因為他要等著西伯利亞的十年流放生活給他以決定性的鍛造。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只擔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令人驚奇的是,他體驗苦難的深度,就是體驗愛的深度。別爾嘉耶夫不無驕傲地說,俄羅斯作家常常因為愛而發瘋。安德烈耶夫、迦爾洵都是這樣的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更加博大的瘋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拿普希金與西方文學大師作比較的時候說:「普希金具有除他之外任何其他人都不具備的特質和天才———他對全世界都抱有悲憫的同情心。」其實,普希金只是這一特質的開拓者,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和托爾斯泰身上,這一特質才表現得更加鮮明更加豐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思想明晰而又確定,他先是因為主張西方化而被流放十年,後來又因為強調俄羅斯民族本土傳統而遭受文化界的攻擊。他在精神上卻更多地表現出猶豫、疑惑、徘徊、質疑等等不確定性的稟賦。他對賭博的癡迷和對癲癇病的眷戀說明他對一切未知事物保持強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他不但熱心於展現底層人的苦難生活,同時也是最熱衷於描寫聖徒精神的作家,可以說他自己就是一位聖徒。可是他是唯一一個同時把對於上帝的疑惑表達得淋漓盡致的聖徒,他極度神經質的敏感幫助他始終處於疑惑的狀態。這些疑惑體現了他對人性的弱點具有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
托爾斯泰是一位生前就被認可的聖徒,受到廣泛的擁戴和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在窮困淒清中孤零零地告別人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