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上公車,便聽到有人在身後叫著,是一種粗氣的男聲,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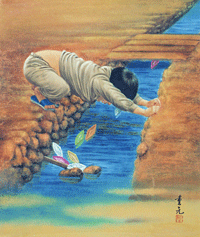 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叫嚷和自己有關。坐定後,右前方的一位理著平頭,上了年紀的尋常男人,側過身對著我大聲的喊著:「太太,你也坐車啊!」看到他的臉,我認出了他是住家附近的家庭理髮師張師傅,心想怎麼這麼不巧,遇到了他。
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叫嚷和自己有關。坐定後,右前方的一位理著平頭,上了年紀的尋常男人,側過身對著我大聲的喊著:「太太,你也坐車啊!」看到他的臉,我認出了他是住家附近的家庭理髮師張師傅,心想怎麼這麼不巧,遇到了他。
我知道張師傅家住泰山,他在我們住家附近巷弄一處老舊的公寓,租了層底樓,入門窄仄的地方擺了兩張男士理髮椅,做為生意場合,裡面暗不見光的空間隔了幾間窄室,以便宜的租金分租。他每天坐著同一路線的公車往返住家,有時,我較晚下班,在回家的路上遇到要回泰山的他,他總會以讓路人側目的嗓音大聲喊著:「你好!你好!」同時高舉著一隻手揮著。但多半時候,我都有意避開他。
我們其實已經認識二十幾年了,避著他,也是最近幾年的事。
二十年前左右,我搬到了現在的住處,記得搬家的時候,由於先生的書太多、太重,搬家工人非常不高興,我被他們的一下要罷工,一下要漲價,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但不管這些家當如何被拋擲,我卻只在乎能夠優先妥善安頓好我的一歲多男孩。在空無一物的新居,我們先架好他的折疊床,然後他便按著自己的作息時間安靜的午睡,渾然不覺已被父母帶離出生的地方。
睡在嬰兒床中的男孩有著白皙的膚色,細細的髮絲服貼著小臉蛋。當他逐日成長,柔順的髮絲覆蓋下來,清秀得像個女孩子,需要修剪時,手拙無法親自為他剪髮的我,在陌生的社區中,找到了張師傅的理髮店,我認為既然是家庭理髮,收費應該比較便宜,對於年輕,收入有限的我們而言,這自然也是一個必須的考慮。
張師傅在他的理髮椅上,架了一條專為小男孩準備的橫木,我的小男孩坐得高高的,乖巧的微微垂著頭,任由張師傅的剪刀在他的髮間撥弄,我從鏡中注視著孩子的神情,一歲多的他有點好奇,也有些微緊張的配合著陌生人的動作,我邊讚美著他,邊和張師傅閒聊著。
巧合的是,張師傅和我都是彰化人,在異地遇到同鄉,自然有些相通的話題。中年的他,聊著在家鄉的父母及兄長,說著他五個年齡不一的孩子龐大的學費,雙手俐落地便剪好一個頭,然後,他會將理髮椅推下,讓孩子躺下,清清孩子的耳垢,省下年輕媽媽的一項工作。那時,張師傅的生意很不錯,小小的店面總有兩、三個客人在等候。
孩子上了幼稚園後,隨著身體的發育,髮絲跟著增多增厚,在張師傅的打理下,留著可愛西瓜皮式的髮型,但這西瓜皮髮型的瀏海剪得太整齊,我幾度被時髦的媽媽唸說,孩子的頭髮剪得太土了,可是考慮到孩子的頭髮長得快,而且收費只有美容院的三分之一,所以便一直在他的店裡出入。
後來,我又有了第二個男孩,相差八歲的兄弟倆便一起出入張師傅的店,年幼的弟弟依樣被剪成西瓜皮的髮式,已慢慢是個青少年的哥哥開始對自己的髮型有了意見,他不願再有瀏海,希望打薄有層次,甚至還試著要分出髮線。但唯一不變的是,他依然很喜歡挖耳垢,因此,練就了一句最標準的閩南語:「阿伯,我要挖耳孔。」張師傅戴起他的老花眼鏡,一邊將理髮椅推下,仔細的在孩子的耳裡掏弄,說著:「這種年齡的孩子耳屎不多,因為有在運動,耳屎會掉出來。」
然後,又說著他的幾個大的孩子都就讀私立專科,學費很貴,間又提起他清明回鄉掃墓,並對鄉人老謝凋零發出一些感謂,他也喜歡說些社區間,我不熟悉的人事,然後又問問我和先生的工作,多半時候,我只是勉力應合著。
後來,我的大男孩上了中學,課業繁重,幾乎只有在學校周一要檢查服裝儀容時,才會在周日用電話詢問張師傅是否有空,我帶著兄弟倆去理髮店,付完錢,便先行回家,張師傅的生意依然不錯,也沒有太多空檔閒聊。然後我的大男孩高中畢業,到南台灣去讀大學,也自然地從張師傅的家庭理髮店畢業。
不過,我還有一個小男孩,當哥哥離家時,升上國小的他依然聽話的任由張師傅幫他打理著西瓜皮式的髮型,但是,當他升上國中時,意識到外表的重要,拒絕再到張師傅的家庭理髮店,改到我出入的女子美容院找年輕的設計師,由於設計師和我相熟,每次便留下他在店裡等候,信任的讓她梳剪。孩子回來後,我總覺得層次落差過大,需要髮膠造型的嘻哈風,實在不太適合國中生,但處在青少年時期的小男孩,卻對年輕設計師的手藝十分滿意,從此,不肯再讓其他人動他的頭髮。
有一次,孩子夜課回來,說明天要複剪頭髮,複剪不過會被記警告。那時,已經晚上九點多了,附近的美容院早都打佯。我帶著他在住家附近尋找還在營業的美容院,找來找去,只剩張師傅的理髮店還開著。他坐在理髮椅上,翹著二郎腿盯著掛在牆上的電視。事實上,好一陣子,我經過他的店,都看到他採這個姿勢在看電視,難得看到他在工作,門口卻多了一塊顯眼的壓克力招牌,用紅漆寫著「理髮一百」。因為,已經好久沒上門,所以我有點不好意思地解釋,孩子現在喜歡剪時髦的髮型。他撥一撥孩子參差的頭髮,說:「這種髮型我也會剪。」然後,我看到他拿著一把老剪刀,提起臂膀,努力的想要在年輕孩子的頭上剪出流行的線條,但不知怎地,孩子的髮型卻恢復了西瓜皮式的味道,只是,這次西瓜皮被削薄了。
那也是我最後一次出入他的家庭理髮店。一年後,我的小男孩升上國二,學生的髮禁開放了,再也不需為學校的服裝儀容檢查,匆匆的去理髮。有時,陪孩子去美容院剪髮,付完錢,告訴年輕的設計師要幫他理規矩一點,他便示意我趕快離開,說他倆會自己商量。當孩子頂著一頭時髦的短髮,抹著髮膠,造型很炫的回來時,我忍不住會說,「這樣哪像學生?」不到十五歲的孩子機伶的回說,「你不要忘了,現在已經沒有髮禁了!」沒有髮禁了,所以女生不再清湯掛麵,男學生也不再用推剪,推出一式的小平頭。
我有時不免也會想起,讀中學六年,最自豪的便是沒剪過清湯掛麵,因為愛漂亮,又仗著功課不錯,從國一開始,頭髮便打薄。有一次,被教官逮到,教官客氣地說:「同學,我知道你表現很好,但你的頭髮這樣不行喔!」我笑笑,依然故我。因為髮禁,當年的女學生高中一畢業,總迫不及待留起了長髮。
關於頭髮的記憶似乎也關乎年代的流轉。
張師傅和我都準備要下車了,他又回過頭來對著我說:「好快啊!我到這裡都已經二十六年了。」我頷著首,對他笑笑,卻在心裡回答他:「是啊!好快,當初我的大男孩到你的理髮店時,才一歲多,如今他已經二十三歲了。」他們早已不再需要我陪同去理髮了。
我們下了車,他拉高嗓音說:「再見,再見!」然後我們各自走開,二十幾年的時光,就這樣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