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涉獵上海城市歷史的人大概都知道,自開埠以來,上海就是一個華洋雜處、古今交錯的地方。一百多年前,大批苦力在江邊碼頭為填飽肚皮流汗,英國殖民者也在為打馬球消遣流汗;一百多年後,天蟾舞台裡水袖翩翩唱著京劇,上海大劇院中同時演出著普契尼《杜蘭朵》的歌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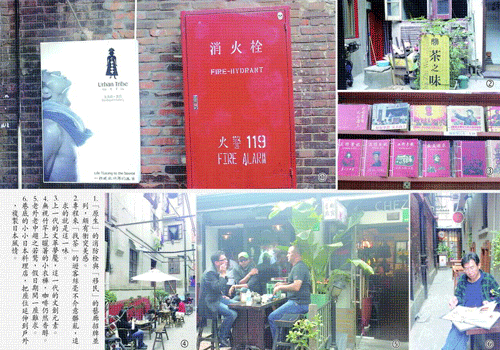
上個世紀末,資本主義大潮席捲上海,歷史及陳舊搖身一變成為商品經濟的新元素,在上海獨樹一格的氛圍中,打造出幾個領先時尚的地標。例如台灣建築師登琨艷在蘇州河邊,改造杜月笙的老倉庫,成為滬台兩地時尚人士嚮往的藝文聖地。再例如香港房地產商羅康瑞把一片石庫門宅子,調理成一杯新天地口味雞尾酒,吸引全世界的觀光客來品啜。
近些年,位於盧灣區的田子坊異軍突起,再創一個立足陳舊、跨越文化的時尚寶地。
其實早在田子坊聲名鵲起之前,著名畫家陳逸飛以及攝影家爾冬強等人,就以泰康路為核心,成立了他們的工作室,漸漸群聚了其他的藝術家,出入於弄堂之間,頗有點「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的味道。
後來進駐了一些年輕人,租下狹窄的民居,開起具有文創趣味的小商鋪,把懷舊情愫包裝成商品,竟然因此引起青睞。好比文化大革命,這場距大陸八○後一代遙遠的歷史事件,到了他們手中,紅衛兵躍上環保購物袋,毛主席的紅寶書(毛語錄)成為隨身筆記本。追溯回三十年代上海的紙醉金迷、歌舞喧嘩,也被他們相中,表現在衣物飾品家居用品,甚至餐飲之中。
隨著上海愈來愈國際化,外國觀光客原本懷抱對東方之珠的幻想,來到這裡卻發現高樓大廈一個個比高度、比現代、比科技,與其他大都市千人一面,毫無特色,此時偏偏田子坊跳進視線,就像一張張泛黃顏色的歷史照片,滿足了他們的上海夢,於是口耳相傳,造就出田子坊的名氣。
與新天地有規畫的開發不同,田子坊的演變就像自然分裂的人體細胞,小店開起來了,人流湧進了,氣息也不同了。藏身在旮旯角的混血口味的餐廳,順著弄堂走道生長,小桌子小椅子露天擺放,如此一來,老外似乎更正中下懷,陽光晴好的日子,紛紛來到這裡,錯把田子坊當成巴黎香榭大道了。
今天的田子坊,街面上幾乎已經完全被商舖占領,僅留少數釘子戶固執的在這裡洗菜、燒飯,吵架、養孩子。他們厭惡探頭探腦的遊客在門窗口張望,樹立起「私人住宅,閒人止步」的告示牌,更帶著「阿拉上海人」的驕傲,鄙夷那些洋鬼子的稀奇德行。說也奇怪,絡繹不絕的觀光客竟也甘心情願,頭頂上竹竿曬著小衣小褲,不以為忤,倚靠斑駁紅牆,聊天喝啤酒吃披薩,看人也被人看,還自我感覺特別良好,覺得一下子擠進了時髦的圈圈。
新與舊之間的界限是什麼?歷史與現代如何區分?在田子坊,沒人問這些無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