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小學時,一篇課文是這樣開頭的:「天這麼黑,風這麼大,爸爸捕魚去,為什還不回家,聽狂風怒吼,叫我心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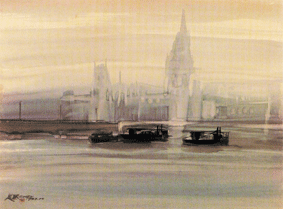 害怕…」。透過這篇文章,海給我初步的印象是負面,不可愛的。儘管老師極力美化海的形貌:「大海生氣的時候,掀起滔天巨浪,人和船都會遭殃,但通常它不生氣,像媽媽一樣溫柔和藹。」
害怕…」。透過這篇文章,海給我初步的印象是負面,不可愛的。儘管老師極力美化海的形貌:「大海生氣的時候,掀起滔天巨浪,人和船都會遭殃,但通常它不生氣,像媽媽一樣溫柔和藹。」
爾後,見到一張圖,題名〈屹立〉,一尊圖柱形建築,面對波濤洶湧的大海,昂然站立岸礁上,海面有幾艘船帆正向它所在方向前進。於是,海,燈塔,與人之間的某種牽連,在我童稚的心中萌了芽。然而直到十八歲以前,我們始終緣慳一面。
這一年,剛通過聯考進入大學就讀,我們刻意於春假造訪了墾丁國家公園有百年歷史的鵝鑾鼻燈塔。燈塔坐落在南台灣鼻頭角,宛若著白色軍裝的海將軍,雄糾糾氣昂昂的睥睨我們這群遠來的造訪者。我好奇地奔過去,招呼:「嗨!大海,終於見到你了。」
鵝鸞鼻三面臨海,南面是壯麗開闊的巴士海峽,天空悠閒著幾許蟬翼的雲絲,遠方漁帆點點,朝向海平線飄遊,海燕披著一身陽光,以極其優美之姿,盤旋於天海之間。有時上衝天際,有時低空掠過。美哉!這大海的一切,雖是第一次照面,我已深深地被吸引,情不自禁地愛上它了。
守塔人引導我們登上塔頂眺望台,並為我們解說燈塔史料:
「塔座建築海拔五十五公尺,高二十一點四公尺,光程二十七點二浬。純導航作用。火力一百八十萬支燭光,十秒一閃。由於居南台灣樞紐地位,其重要性位居台灣目前所有的三十幾座燈塔之首。」
透過窗櫺極目擴展視野,海界無垠,天高雲淡,若鷹盤踞蒼穹,眼界頓時廣邁清明,回首偷偷窺視守塔人,歲月風霜在他剛毅的臉上鑿下紋路,曾經多少辛勤的汗水流過這些痕溝?最難忍的恐怕是寂寞與孤獨吧!是什麼樣的犧牲奉獻情操才承受得住這份沉重。燈塔若沒有守塔人,就如同唇亡齒寒,無人掌控光明,就只空剩一具軀殼了。人就是塔,塔就是人,是一體不可分割的,我這樣認為。
梅爾遜的《白黥記》,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李查巴哈的《天地一沙鷗》,分別以不同的筆觸展現海的多重性格及善變面貌,溫柔時宛如陰柔女神,神祕、浪漫、美麗;憤怒時如魔王發威,火爆剛烈,掀起波濤巨浪,將人翻覆手掌中任取性命;海象徵著大自然神聖不可侵犯,在它面前人真是滄海之一粟,儘管它敞開胸襟任意人類擷取乳汁,而美麗的背後卻隱藏一股無情的殺意,對於討海人,海是礦場也可能是墳場。燈塔不妨看作人的一種企圖,一種與大海抗衡的企圖,企圖以最少的人命犧牲取大海斐然的寶藏。
再度邂逅燈塔,及其屹立的海洋,已是婚後定居港都高雄的事了。
與西子灣港區一水之隔的半島旗津,其北端旗后山上的「旗后燈塔」,西望婆娑台灣海峽,水色深藍,波光瀲灩;東邊遙瞰鼓山,共同扼守高雄港喉舌。清朝到民國,歷百餘年歲月風霜,始終堅守崗位,善盡其職,日日夜夜朝向大海,面對進出港口的船隻,指揮若定。
那是初夏時節,一家四口相偕由高雄港搭台華輪出航,前往天人菊的故鄉———澎湖暢遊,享足拾貝,撿海星,堆沙,踏浪,海泳等一串活動的樂趣。遊畢歸來,適巧颱風過境,天候大變,整個海域誨暗陰沉,船在驟雨狂風巨浪中巔簸前進,身歷其境小學三年級那一篇課文。七暈八吐後,緊閉雙眼,蜷伏床鋪,整個人恍惚沉溺在風的控訴,雨的哭嚎與浪濤咆哮漩渦當中不得抽身。不禁欽佩不時得與海搏鬥海的子民,他們的健碩體魄,他們的堅忍不拔,為了生活,為了家人,勇敢挑戰大海,通過大自然對他們的考驗。
「快到港口了。看!那是旗后燈塔。」外子一把拉我起身,擠向船窗。
「啊!燈塔在向我們眨眼呢。」浮躁害怕的心情逐漸安定。順著外子手指方向,遠方天際一環仙女棒似的火光瑩瑩閃動,那不是一盞燈嗎?為夜歸人預留的一盞燈?
船穿透黑幕,破浪前進,迎向光亮,閃爍的光圈漸漸擴大,光亮愈來愈強烈直到凌空消失,原來船已經游過燈塔足下,進入高雄港,準備靠岸新濱碼頭。到家了,回家的感覺真好,那些討海人,歸來時望見燈塔,必然也是這樣一個心情吧!捕魚的爸爸終究帶著漁獲回家了,因為有了燈塔照亮來時路,指引歸途。
燈塔,就像當年媽祖默娘手上那一盞燈一樣,對於討海人肩負一項精神意義。那就是信(信心),望(希望),愛(守燈人的犧牲奉獻)。
海,燈塔,人,有著必然牽連,我終於徹底領悟。?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