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肥火車站見面,吃一餐飯,那樣時空遙隔後的初見,似就是為了一餐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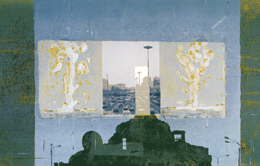
匆匆忙忙地,記不得那個飯店的名字,或許也是根本無暇去顧及。來不及顧及的,還有幾個姓名,大媽的、大嫂的姓名都不知曉,只知道幾個小孩一一報名,鹿慧,鹿旭,王小鹿。
六十年前,可能是陰雨的春天早晨,可能是炎熱的夏天傍晚,剛滿二十歲的父親吃過一碗很辣很辣的安徽麵條後,經過合肥車站,再到南京再到杭州再到上海,到了台灣。二○○九年夏天,也是在合肥車站,從未謀面的有血緣的幾個人,相約在車站前的麥當勞速食店門口,第一次知道同父異母的兄長原來在一九四七年就出生了,過了耳順之年有些駝背的他,仔細在盤算自己與妹妹差幾歲。
安徽老家一直說奶奶還在,父親回家探親,大娘比當年的奶奶年紀更老了,而奶奶是一堆很久很久以前的小墳了。父親見到已經過了不惑的兒子,天涯成咫尺,父子在手足無措下相處不到兩天,好像就談不下去了,時空距離太大,一時不知如何說起,嗔癡怨太深,千言萬語也說不盡。原來,相見相處才知咫尺正是天涯。
一九八九年開始,走遍了大半個中國,陝西、山西、雲南、四川、廣東、廣西、江蘇、浙江、河南、山東、北京、上海,經過二十年,終於進了安徽的省域。蘇州在春天的晨曦中醒來,十全街上的梧桐樹凍掛著一溜水珠,春寒料峭的蘇州桃花開著,攝氏八度或九度的低溫在台灣是寒流來的表徵。回頭看了一眼下榻的東吳飯店,是當年公瑾的東吳,而你如今要到潁水之濱,有人叫潁濱遺老,叫東坡的人在那遺落了青春。
一路默念熟悉的站名,無錫、常州、鎮江、南京、全椒,於是,合肥車站到了。你是代替父親回鄉嗎?
學校的同事在合肥西郊的小團山經營個安身立命的香草農莊,你到那個小團山的世外桃源,雨濛濛下著,大片落地窗外是紫玉蘭花,遠處則是黃澄澄的油菜花,更遠的遠方長長一列火車消失在黃澄澄的油菜花田後,將春天的花田帶往武漢去。這就是安徽的土地了,父親的淮河,父親戲水的童年,父親喜歡的油菜花。
你斷斷續續地,漫不經心地打著電話,一次次慶幸著,無人應答。突然害怕另一頭自己不熟悉的鄉音。父親生前,老是埋怨自己聽不懂兒子的安徽話,是時間太久或空間太遠,讓彼此再無交集的可能。
在有濃濃歐風的香草農莊,喝薰衣草茶,想著金門高粱、台灣炒米粉在這個劉銘傳曾經練兵的地方出現,而劉銘傳不在家,他去了台灣,台灣出現銘傳小學,也出現銘傳大學。旁邊的劉銘傳故居只剩下幾棵烏←樹與玉蘭樹,有一棵樹相傳是慈禧太后賞賜的,樹又抽了新芽。
電話通了。大哥說人都到了合肥就回家裡來吧!在電話中爭執許久,阻止他們開車來接,大哥在另頭忙不迭嘮叨,四個鐘頭就到了,很近的,很方便。是的,四個鐘頭是台北到高雄,像是你每次的返家。
一九七九年夏天,在一個叫九曲堂的小車站,父親送你負笈台北讀大學。鹿家第一個上大學的人,父親說。每隔幾個月,學校放寒暑假,父親說回家吧,包餃子給你吃。你一向對餃子素無好感,對父親酷愛的蔥薑避之唯恐不及。而父親的獎賞就是包餃子吃。
在合肥車站前,叫鹿剛的男孩走來,帶著靦腆,毫無遲疑地大聲喚「姑姑」,你們似乎馬上就辨識出彼此,緣由都有如父親一般的眉眼,接著,大哥來了,一群小孩來了,而後一個長得與父親頗相像的女孩背著大娘來了。印象中的男孩女孩在父親返家時拉扯著不讓爺爺走,現在已經為人父母,各自拉扯著小孩。
女孩叫春梅、叫莉莉,爺爺不滿意她們的名字。父親一生,行事不與流俗同。小男孩走近自我介紹,叫王小鹿,春梅說爺爺取的。不能逼人姓鹿,只好硬給人取名小鹿,你看著車站前的人潮,心裡想著父親。合肥車站前首次晤面的黝黑小男孩,喚起對父親霸氣的印象,一生陷在不得意的情緒裡,沒有安全感,找不到舞台。
在合肥車站見到了鹿家所有的人,包括鹿家的女婿。而大部分的人與你用同一個姓氏,甚至有雷同的長相,叫鹿慧、鹿旭。一大家子的人,也許你以前就見過他們,那個叫鹿慧的小女孩,六歲,你小時就長那個樣子吧?圓圓的一個包子臉,可愛極了,你想起自己小時的綽號,被叫麵包。而鹿旭讓你震驚,曾經,你可能會有另一個兒子;當肚腹漸漸隆起,你要取一個名號,旭兒。鉅大的傷痛過後,你告訴兩個準備當姊姊哥哥的曙兒、曄兒,也許緣分不夠,到別人家了。七、八年了,你看到與你神似的旭兒,親熱地喚你摟你。原來,有個旭兒在鹿家,他五歲了。
報上說,安徽許多名菜都有故事,劉銘傳酥鮑、周公瑾魚頭、曹操錦囊雞、華陀長壽湯、劉伶酒肉香、胡開文墨糕、李鴻章大雜燴、劉安點豆腐、胡適一品鍋、紅頂問政筍、包公酥鯽魚等。你點的菜沒有故事,是一頁難以言說的家族史,是一齣難以言說的時代劇。
一餐飯吃了好久好久,像是地老天荒,橫跨六十年,從此岸到彼岸,渡河渡江渡海。桌上放眼是紅豔的湯汁,辣椒,辣椒,還是辣椒,父親的餐桌都是辣椒,炒的爆的或是生鮮的,他拿在手上,啃著。回到父親的皖北,吃了一餐辣椒全席,辣得一臉,全是紅淚。父親,離開好久好久了,大娘,一句話也無。臨走,她揪著不停問,怎不回家裡去?解釋著,她聽不到。快九十了,耳朵完全不管用,你想像不出,父親離開,她二十幾,懷著孩子。掙脫大娘的揪扯,像逃難似地,又擠進合肥車站。站在月台,看了一下春日的略帶暖意的夕陽餘暉中一張張臉,只覺得,地方熟悉得很,也許,以前來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