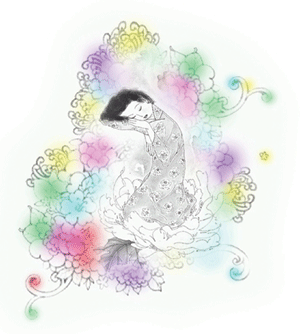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陰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陰
今天是臘月二十九,除夕。
凱兒沿濱海公路去新竹接海北的大姐河北,我往台北去接我的大姐慕德,對孩子們來說,大姑姑和大阿姨來我們家過年,總是會讓這個家更顯熱鬧,更像過年。
車過士林、劍潭,再上新生北路高架橋,直奔和平東路,一路都很順暢,大概很多人都已經回南部了。
一路過來,幾乎每家店舖都關門歇業了。那原本應該是很難看的鐵捲門,卻在除夕這天顯現出一種很平和很安靜的美感。
這是偃旗息鼓的一刻,讓我心安。
想著從北到南,在此時此刻,都處在同一種文化同一種信仰的氛圍裡,不再去管誰綠誰紅誰藍,這是除夕,我們都願意遵循這樣的規矩,只想要和家人團聚,好好吃一頓年夜飯,好好過一個年。
原來,我們和左鄰右舍都如此相似,這樣的領會讓人覺得幸福(幾幾乎是太平歲月的那種幸福了)。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晴
想念A,但是,他上次留給我的通訊地址和手機號碼的那封信,不知道又被我收到那裡去了,怎麼找也找不到。
翻開二○○四年的日記,十一月十號那天早上接到的電話:「電話響起來的時候我應該是已經醒了,海北也是。只是電話來得太早,我們都很驚訝,原來是A打來的,時間還不到八點。
他說,十三或十四號就回去了,這幾天因為應酬太多,日子都亂了,所以,不來我們家,只決定給我打個電話。
他知道我膽結石開刀的事了。
幾句之後,忽然說起他的回鄉。
他說,他十七歲離開家之後,過了四十二年,才能再回老家,應該是五十九歲了。
他說,就像古詩〈從軍行〉裡的那個老兵,十五歲離家,八十歲回鄉,採院中野菜烹煮,熟了之後,不知道要給誰吃。
他說,舊家只剩下一塊洗衣漿衣之後的擣衣石,一塊平滑如几的青石。
舊屋也只剩下一堵牆。
他寫信要堂弟千萬別拆除那堵牆,等他回去憑弔。
然後,拿出兩萬人民幣,再用記憶畫出了舊家的圖,在從前的地基上蓋了一樣的一棟新房。
(他說,當時「台胞」吃香,所以一切順利,甚至強占了隔壁老鄰居的一些地,後來被A發現之後,趕快叫他堂弟拆牆,退後復原。)
他說,老家有祖墳,爺爺奶奶、父母與叔嬸都安葬在此。但是,事實上,祖墳之中只有三位女性的骸骨,三個男人都是死在外地,父親死在青海勞改營,爺爺在外工作時被土匪殺死,而叔叔是被共產黨所殺害的(臆測是在福州)。三個男人都沒有回來,墓中埋葬的只是象徵性的衣冠。四十二年之後,A在墳前為這個家族立下墓碑。
三個男人都沒有回來,嬸嬸去世之後,A的母親撫養最小的堂弟長大。
他說,最近一次,又回家鄉,在母親墳前和母親說了一些話,他說:「娘,你四十多歲就過世了,現在我已經七十多歲,比你都老了。」
他說,共產黨不殺知名人物,頂多是命令他寫悔改書,有用時再拿出來給世人看,表示此人還在,但是,卻專殺無名百姓,成千上萬。
A的聲音,在電話中一逕是沉厚平穩,悲傷也不顯露,彷彿在說著的是他人的情節,然而,這是什麼樣的人生呢?
這是什麼樣的人生?
他說,他的作品卻從來沒有觸及自己的痛苦,寫出自己的遭遇,因而覺得內疚與無奈,可是,有些感受,又不敢去觸碰。
我在電話這邊,不知道該要怎樣去安慰他。不過,放下電話之後,我卻想要告訴他,那深沉的悲傷,其實是遍佈在他的作品裡,以一種聲東擊西的方式宣示她的存在。
可是卻找不到他的電話號碼了。」
所有流離失所的記憶,不管是牢牢記住的或者是忘記了的,對每一個生命來說,都是暗傷。
這暗傷,讓我們終生啞口無言,但是,那在文字中不斷閃現。
過去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可是,那在過去的時間裡所造成的悲傷卻始終存在。
所以,時間消逝,悲傷卻以固執頑強的姿態停留了下來,戴著面具,潛入A的每一篇作品裡。(四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