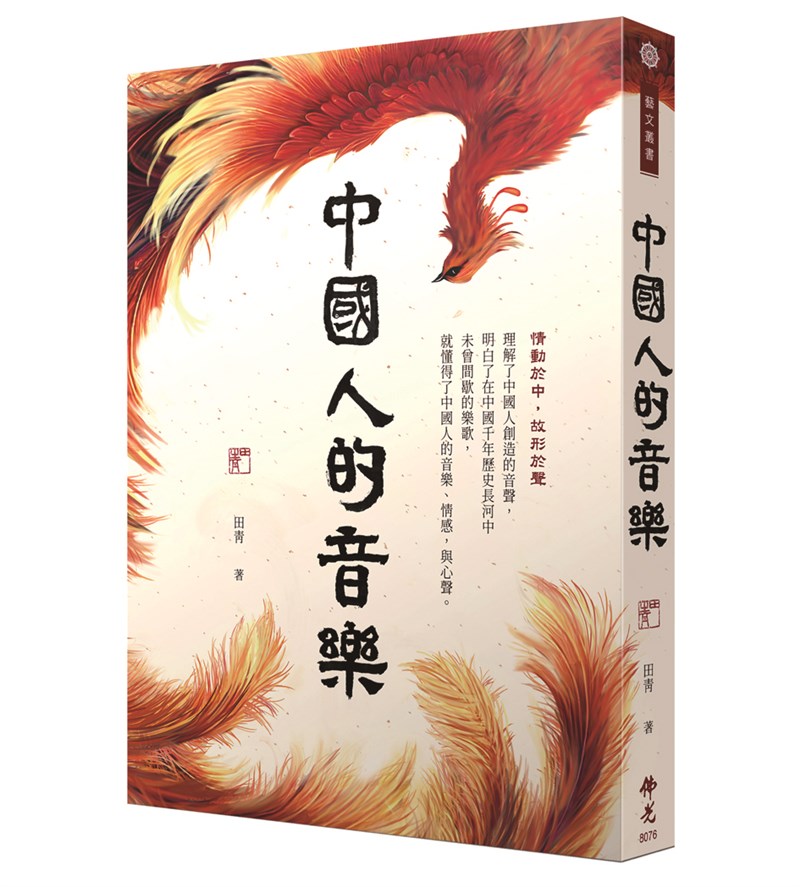 圖/佛光文化提供
圖/佛光文化提供
文/林谷芳
要說二十年來引領大陸社會對中樂有不同觀瞻的頭號人物,真非田青莫屬。
原來,相較於與其他藝術,音樂有它更自洽、更接近自然數理的屬性,也由於它的抽象,所以用文字談音樂,往往開口便錯,這一方面使得許多樂評與音樂介紹常華而不實,另方面,音樂又牽涉獨特的技巧——尤其在器樂,門檻既高,音樂家常自然地就在一個相對封閉的領域裡自我發展。於是,真談外界對音樂的認知,更多就停留在社會的習見上。
然而,田青在二○○○年第九屆大陸央視青年歌手大獎賽對「罐頭歌手」「千人一聲」的批判,卻以其直率而具說服力的評語,直批習見,透過大眾媒介,引發了社會的高度震撼,以致於在後來的「青歌賽」中就有了「原生態」唱法的分組設立,而社會大眾也透過這些民間歌手既質樸且精鍊的歌聲,直接觸摸到不同族群的真實生活,其所引致的感動正是所謂的「專業表演」所難以企及的。
而此同時,大陸又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開始了大力保護。原來,大陸之前對「非遺」是極端陌生的,但由於政府的大把給力,以及有著田青這等實際掌舵的人,竟在短短時間內,就讓「非遺」成為琅琅上口的日常用語,以致於,如今的大陸,儘管在「非遺」的認定上層層把關,但只要跟傳統文化沾點邊的,許多人也就直接用「非遺」來粧點自己。
客觀地講,對「非遺」的保護,是大陸二十年來文化復興的一個亮點,而其間用力之勤、觀瞻之深、影響之大者,田青當數第一,而也藉由這個「非遺」熱潮,他讓許多人改變了對傳統音樂的認知。
其實,儘管一直強調民族文化,大陸對「非遺」的認知在本世紀之前也還基本空白,而就在此時,田青受邀來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位於宜蘭的傳統藝術中心當時正在興建,有許多對「非遺」的觀念與作為正在此地激盪著,主要執事者之一也恰在藝術所進修,據田青稱,這段宜蘭經驗直接觸動了他對「非遺」保護的許多思索。
沒想到的是,之後的他有機會在大陸風起雲湧地推動這項工作,而台灣卻相形見絀。不過每談及此事,他也總會提到與佛光山、佛光大學藝研所,以及我這位老朋友的這點因緣。
正如此,以田青之動見觀瞻,若要寫一本中國音樂的書,外界的想像,當然是高屋建翎地直顯他豐富的學識,系統姓地說明中國音樂的特質及其在世界文化版圖上的地位,可田青卻即此不為,他竟直接以自己的生命經驗寫就了這本《中國人的音樂》。
從標題看,《中國人的音樂》是本具有概論意味的書,而也的確,書中三大部的「樂器與器樂」、「聲樂與民歌」、「新音樂」可說含賅了音樂的主要塊面,讀者從中對中國音樂可以得到整體的印象。然而,與一般概論書根柢不同的是,概論性的著作講究的是全面、原則性的掌握,讀起來很難直面作者的生命情性,但《中國人的音樂》不同,儘管範疇全面,卻就是從田青直接的生命經驗中寫出來的,每一個他介紹的塊面,都是他親自領略乃至挖掘的,也因此就深深有別於一般概論性的介紹,或抽象性的美學陳述。
為何會如此且能如此呢?深厚的學養、紮實的田野,以及這二十年領航「非遺」,挖掘被大家忽略卻又有著無比衝激力的民間樂人,跟他們還有生命性的交往,這些經驗都是別人難以取代的,由是,他充滿情性的書寫,直顯的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談樂如談禪,基本「開口便錯」,再多的理論,都不如直視那真實可觸可摸的生命,以此,讀者也才能知道作者想跟你分享、跟你共情的是什麼。所以書名就叫「中國人的音樂」,畢竟,人,才是核心。
也因此,儘管將此書結構性地分為三大塊,但在談任一主題時,他無不「以事顯理」,就用活生生的作品、活生生的樂人,以及他自己活生生與活體傳承者的因緣,娓娓道出音樂中的生命情感、生活特質,以及藝術特徵,雖各自單獨成篇,卻無不完整,字裡行間流淌的情懷與觀照始終串聯其間,也就在這樣的敍述中,一件件樂器、一首首經典如琴曲〈流水〉、二胡曲〈二泉映月〉、管子曲〈江河水〉、箏曲〈崖山哀〉、琵琶曲〈霸王卸甲〉,以及一個個他接觸或瞭解的音樂家,從楊蔭瀏這樣的前輩學者,到左權的盲藝人,以迄新音樂的作曲家,乃都躍然紙上,而在充滿「人味」的介紹中,讀者對這些音樂與音樂家也產生了親切與景仰感,田青希望大家能親炙的文化瑰寶乃自然地烙印於讀者心中。
的確,「以事成理」是本書的特色,但這「事」既連接著田青個人的文化角色,雖由此而讓所敍更加生動,責其全者,恐怕也還是會擔憂,一不小心,作者是否就難免於其當代乃至時潮的局限。好在,回到藝術的原點,仍舊是田青這位藝術家念茲在茲的,例如他提到〈江河水〉、〈二泉映月〉過去官方解說的局限,強調須放在歷史長河、人性觀照上來更精切地理解經典就是個例子,而對於宗教文化被狹隘片面式解讀的提醒,也可見在澎湃的民族情懷下,他對文化或藝術原點的觀照與堅持。
正是有著這些特點,作為一個專業的音樂工作者,讀起此書,你會感嘆於它的淺出正由於它的深入;而作為一般的讀者,不知不覺間也就有了中國音樂提綱挈領、具體而微的全境圖,從此正可按圖索驥,直接前往。
我與田青結緣甚長,在一九九○年代的兩岸音樂界,我們都比較是非主流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始終把音樂當成文化的一環來看待,以此而深入一個族群的生活、情感乃至思惟。而在台灣,我自己多少也扮演了一定角色。
然而,以大陸之大,即便是田青之才,要真能發揮文化的槓桿作用,還須有外在的時節因緣不可,諸緣兼具,再加以田青振聾發聵的獅子吼,以及往後的政策推行,終於造就了在台灣難以想像的文化波濤。即此,還不得不感嘆於因緣的不可思議。
這樣的一本書,要在台灣出版,緣於對文化的觀照,以及對因緣的體會,身為老友,所寫也就不僅僅是個評論或推薦文章,而是更希望大家能由此認識這樣的一位文化人、音樂家,他心底的情懷,以及因這情懷結諸的有緣,至於有人因書而能對中國音樂有深的觸動,那更就不在話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