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偃,字子游,魯國人,小孔子四十五歲。他使孔子以禮樂之道教化的理想,得到具體而真實的驗證。有一回,孔子帶著一群大大小小的學生到武城去。聽到了滿城弦歌,他微微一笑地說:「啊!殺雞何必用牛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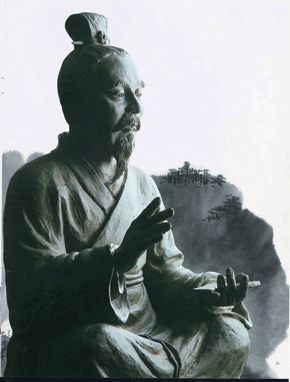 子游當時是武城的宰官,聽說這話,滿臉敬謹的辯解道:「老師以前不是說過:在位的人學禮樂,就能愛人行道;一般小民學禮樂,就能遵行禮法,中心平和,易於使令。」
子游當時是武城的宰官,聽說這話,滿臉敬謹的辯解道:「老師以前不是說過:在位的人學禮樂,就能愛人行道;一般小民學禮樂,就能遵行禮法,中心平和,易於使令。」
孔子看著這位年紀輕輕、認真在意的學生,回過頭來對其他人說:「偃的話說得是,我剛剛是開玩笑的!」
孔子一生,周遊四方,他提倡的「道」,終究沒能得到推行,老來回到魯國,刪詩序書,訂禮正樂,想來無窮的心願,只能寄託於未來。沒想到一到武城,忽聽得弦歌盈耳,不禁心頭一開,滿懷歡喜之情,化作戲言,他一方面惋惜子游大才小用,把治國平天下的禮樂大道,用來治這個小小武城;一方面對子游信道之篤,深深欣慰。師弟一行人,談笑之間,和風惠暢,猶如天地春生。
在十哲中,子游位列「文學」,文學指詩書禮樂文章而言。他傳禮樂的遺文,集詩書的實學,是真正嫻習於禮樂,優游於詩書之人。我們從《禮記‧檀弓上下篇》之中,可以看到當時公卿大夫士庶人,凡是討論禮而不能裁斷的,都常常要以他的一句話為輕重。他的「知禮」,在當時是具權威性的。他明白先王制禮,都依於人情,具有深意,只是到了後代,亡失了禮意,儀文變成了徒具形式,所以,根據《禮記》的記載,他能把儀文的內涵,說得明通而曲達人情。
例如有一回,有子與他看到一位男子,因思親號哭而呼天搶地,有子表示終於明白喪禮中有「踊」這種禮。子游就說了一段先王制禮的用意:「人一歡喜就有快感,然後出口歌詠,然後動搖身體,然後舞蹈;一悲哀就慍怒,然後憂戚、歎息、撫心,然後跳踊。先王因人情而立節度,讓它有等級、有裁限,所以情感不會過與不及,這就是所謂的禮。」
他不但嫻熟禮樂,而且還有知人的特識。當他做武城宰的時候,孔子特別垂問:「得了人才沒?」他答道:「有一位澹臺滅明,他絕不抄小路、走捷徑;不是公事,從不到我房裡來。」
這等人,在一般人看來,是個迂腐而不討好的人,獨獨子游見識得到他行趨的端正,持身的方直,是個有道的君子。王船山說他:「以文學治小邑,得到的是質樸勇決之士,這是君子儒。」
另外,他的知人之明,常寄託在道義相勉的「師友之義」當中。他愛重子張的才高度大,期勉他能更進於仁;怕子夏泥於灑掃應對進退的末節,特別指出教學宜著重大道之本,他用心切磋,建基在對聖人「道體、道用」的領略上。
《說苑》上有一段記載:季康子問子游:「仁者愛人嗎?」他答:「是。」「那人們也愛他嗎?」他再答:「是。」康子說:「鄭國子產死,鄭國人男子不佩玉,女子不戴耳環,大家在街巷中哭,三個月間沒有人奏樂。可是仲尼去世,我沒聽說魯國有這種光景,是怎麼回事?」
子游於是分析:「就好比溝渠裡的水,得到它灌溉就活,得不到就死,作用是立即的;子產的惠澤就是這般『小德川流』,所以鄭國人擔心沒有人可以接續他的善政。而孔子呢,就好比天雨,惠澤普及於生民,而人們渾然不知,視作平常,這是『大德敦化』,人們時時依靠它活命,卻又不知珍惜。」這位後起之秀所傳的,又豈止是詩書禮樂的文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