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子名回,字子淵,魯國人。是孔子門下較年輕的學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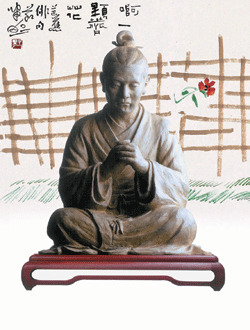
他終日陪侍在孔子的身邊,靜靜地聆聽教言,沒一句問難的話,彷彿是個愚人;可是觀察他私下的言談舉止,卻又能暢發夫子的旨意,他不是真愚,他是大智「若愚」。他對於孔子的訓誨,心解力行,永不懈怠,孔子稱讚他「好學」,他好的是上達聖人之道的學啊!
勘驗於生活上,他雖然吃一小筐子飯,喝一瓢子水,住在簡陋的窄巷中,過著一般人所不堪的生活,可是卻樂而忘憂,這種樂,不是由知解而得,是從真實的道德實踐中得來。換句話說,一個人如不經過這一種真實生活,就不可能體驗出個中的樂趣,所以孔子讚歎他:「賢哉回也」。
勘驗於個人的修為上,他「不遷怒、不貳過」。人們做出的「事」,若用「理」來評量,少不得有不合理而可怒的,如果遷怒於另一個人,平白使不相干的人難堪,那就是不仁酖酖不仁的事,顏淵不做。又,《易經繫辭》下,孔子曾提到:顏氏之子,遇到自己微有差失,便能自我省察,省察後,絕不犯第二次,所以不貳過建立在自省與決心上。
總之,他擇定了天下的正道酖酖中,天下的定理酖酖庸,作為修養的準則,只要知道那是善的,就懇摯地存在心胸中,時刻都不放鬆。所以在孔子群弟子之中,只有他「三月不違仁」,三月表時間長久,也就是他經年累月地不會離開「仁」,既然仁在內為主,居於仁的安宅之中,任何事都從這片仁心發出,自然表現得一派溫潤的天和之氣了。
曾子曾經帶著企慕的心,讚美他:「自己才能高,而能向較低的人請教;自己見多識廣,而能向見識淺陋的人請教;雖然內涵豐富,卻好像了無一物;雖然充實,卻好像空虛;就算別人無故衝犯他,他也是不予計較。」
他這種平易謙沖的風度,是因為從他眼裡望去,別人再怎麼樣,總有一些我沒有的優點,我自己也一定有一些不是的地方。於是,言志時,他希望「無伐善、無施勞」,不矜誇自己有能力,認為那是我該具備的;不張大自己有功勞,認為那是我該盡力的。陸象山盛讚他「最有精神」,程明道也說他「默識」,他的心,純純粹粹,就沐浴在聖人的大道中。
在《韓詩外傳》、《說苑》、《孔子家語》中,同時都記載一件事:有一次,孔子北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隨侍在側,孔子讓他們談自己的志向。子路對舉兵攻城略地,有一番奮勇激憤的言論;子貢對陳說於兩敵之間,解兩國之患的折衝往來,也頗有自信;獨有顏淵退而不對,孔子再問,他才說出他輔佐明王聖主,敷陳五倫教育,以禮樂來化導,使人們能各得其所的德化理想。孔子讚歎他姚姚乎美極了!從這裡,看得出他政教方面的懷抱,只可惜有禹稷的才能,卻沒有禹稷的時機,只好「舍之則藏」了。
顏淵死時才四十一歲,孔子哭之慟酖酖明明一個傳他大道的人,竟然早他而去,他只能傷心地說:「是老天要亡我!是老天要亡我!」後來在元、明時,帝王封他作「復聖」,也算是後代對他的德行,有一番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