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畫的取位在反映人類生活,以擷取現實生活為題材的「水墨人物寫生」,要畫好不易。在繪畫的觀念裡,畫什麼對象並不重要,也不一定要選擇具有偉大事蹟者或社會名流為對象。重要的是怎麼樣畫,及能畫出什麼樣的圖象,能不能表露現實精神的人物獨特性情,和在繁雜社會生活中的人物特殊意義,這是畫家他在審美意識與視覺感受對客體入畫的選擇。因之,老教授、苦行者、原住民、勞工、兒童、小販的身影,就成為我捕捉的習慣思維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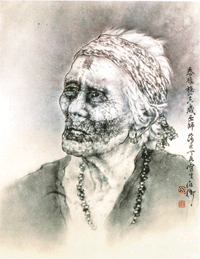 「泰雅莎巴」就是在我這種平凡的觀念下,於一九九七年她已年高一百零六歲時為她所寫的水墨畫肖像。在她緊鎖的眉宇,有誰深入理解她深植著一種部落使命感的思索?在她那微迷縮視的眺望眼神裡,似乎隱藏著回流心中的淚光,有多少人能體會她下決定虔誠執著做一位女巫師的心靈?在她滿臉勒刻纏繞的皺紋和雙頰深重的刺青,何人能瞭解她智性的孤獨人生與烙痕?她那鎮定力度的緊閉雙唇,又有誰能體會她一生心底永不休止的禱念和無聲的吶喊?
「泰雅莎巴」就是在我這種平凡的觀念下,於一九九七年她已年高一百零六歲時為她所寫的水墨畫肖像。在她緊鎖的眉宇,有誰深入理解她深植著一種部落使命感的思索?在她那微迷縮視的眺望眼神裡,似乎隱藏著回流心中的淚光,有多少人能體會她下決定虔誠執著做一位女巫師的心靈?在她滿臉勒刻纏繞的皺紋和雙頰深重的刺青,何人能瞭解她智性的孤獨人生與烙痕?她那鎮定力度的緊閉雙唇,又有誰能體會她一生心底永不休止的禱念和無聲的吶喊?
這些我內心的自問,閃現在「莎巴」女巫身世的橫斷面,成為我對她畫像時以形述情的內在探索。
首先我捨棄光影,也利用光影:我捨棄重色調作為「消色」背景,也不想從人類對宗教的原始意識角度去詮釋「莎巴」畫成一幅宗教繪畫。而是從物我昇華的藝術觀所起的作用,去刻畫一位泰雅族國寶的女巫平實純樸的側影。
深灰的背景、虛化的流動側光,對她臉部進行聚焦表現,嘗試將一位具體可感的形象,放置在一個等觀的古老文化歷史時空中,從而讓觀者對泰雅族的百齡女巫在世俗的生活中,虛擬出理性神秘的視覺和心理反映。
但當我在構思造型的筆觸和技法擔負著言說「莎巴」時,創作思維意會自己要準確落筆,把握神態和平淡天真的意境,在墨痕中略施微染,不要太「放任自流」。唯接續而來的筆墨延伸卻加重我指向性的創作意念:如何凝固人物瞬間動態,表現它的體積質量、情緒與個性的綜合呈現,讓「莎巴」她的面影成為泰雅族的故事,和原住民古老文化的遐想,是藝術意念的表現,而不是應物象形的描摹。
原住民作為現代社會人類關注的焦點,可以給人無法估量的內涵外延,我想從立體的視角去觀察台灣原住民的獨特人文風情;以此去感受原住民歷經艱辛的荊山棘道的跋涉,在一個時代裡最先踏進原鄉大地的印痕所具的象徵意義。也以此去感受原住民樸實熱誠、堅毅勇敢與粗獷豪放個性,在昔日深山荒野無法掩沒的苦澀韌性人生,和從他們族群的高亢狂舞歌聲中傳達不抱怨地易予滿足生活的情采,是否就是一種人生的境界?
這些在我心中突萌的種種疑問,無一不觸動藝術思維去迎接對人們心靈產生的撞擊,蘊意致深的物象。也形成我傾聽南澳鄉長江明順先生為我驅車導覽金岳村泰雅族的「莎韻」碑亭,一路深具內涵的閒聊,和他所觸所感的心聲,交聚成為我筆墨的訴說。
畫人物最忌「見千人如一面」,畫山水最怕「寫萬山如一山」。水墨寫生人物要傳神、生動,只有實踐再實踐,從刻苦鑽研及不斷思索中提高悟性和熟練技巧。在現實社會,走別人走過的路是便捷省力,在藝術生活,跟隨別人走過的路,則將陷入泥沼永難走出。
是因寫生人物是靈感自覺於物象的肯綮,其形式、技巧只是如同文學寫作中的鍊詞造句,是服務於新的靈感形式造型,是「意度」的修為。關鍵是要把這些詞句匯寫成為文章,這就不在於繼承和發掘古人留下的技法與趣韻,也不在於把西方繪畫解剖去扭曲詭異變形,更不在於為與西方「接軌」,製造類似異國文化可能認同的形式,更無須製造驚世駭俗不適官能心性之作,掩飾被自己溶解的觀念。
因為藝術的過程不是毫不受制約的自由表達,它是基於對文化的理解與經驗而形成的自由表達及清晰的判斷。在藝術的背後,它是一種勞動、探究到成形,並通過諸多藝術法則才漸趨成熟。但成熟並非最後階段,它是另一階段的起點,它標誌著形成階段的結束、創造性發展的開端。
(「泰雅莎巴」75x67公分
獲文化藝術薪傳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