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演王小棣認為國片雖生存不易,但仍有發展的空間。圖/大塊文化提供
導演王小棣認為國片雖生存不易,但仍有發展的空間。圖/大塊文化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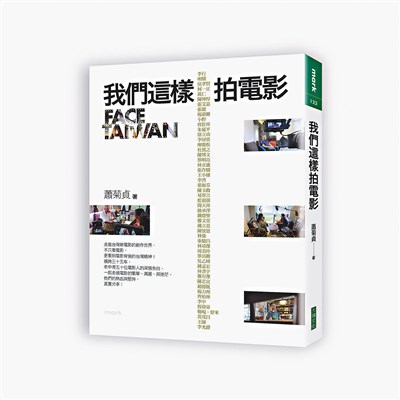 我基本上覺得電影是一個跟社會互動、跟生活互動、跟你整個國家的情勢、你的文明程度等等互動的。
在二○○一年這一整段時間,台灣電影最低潮的時候,我記得那時候幾個年輕人仍然在做「純十六」,而我們在那個最低潮的時候,很多時候是非常受打擊的。圖/大塊文化提供
我基本上覺得電影是一個跟社會互動、跟生活互動、跟你整個國家的情勢、你的文明程度等等互動的。
在二○○一年這一整段時間,台灣電影最低潮的時候,我記得那時候幾個年輕人仍然在做「純十六」,而我們在那個最低潮的時候,很多時候是非常受打擊的。圖/大塊文化提供
文/王小棣
我基本上覺得電影是一個跟社會互動、跟生活互動、跟你整個國家的情勢、你的文明程度等等互動的。
在二○○一年這一整段時間,台灣電影最低潮的時候,我記得那時候幾個年輕人仍然在做「純十六」,而我們在那個最低潮的時候,很多時候是非常受打擊的。譬如說你去看你的電影上演,就像一個笑話一樣。我記得我在戲院對面吃冰,老闆說:「你在看什麼?」我說,「我的片子上映了。」他說,「國片啊!那沒人要看,要看就看錄影帶就好。」
我們經歷的就是這樣的時代。可是我感覺那個時候,我身邊不管是前輩,或者是年紀小的,沒有一個人說因為票房不好,就不想(拍電影),沒有。我們依然覺得不然試試這樣做,不然那樣做,做各種形式的努力。而且我覺得那個時候剛好是紀錄片也比較有作品出來,然後動畫也是,那個力氣一直在。
這一段時間的好萊塢大片很多,大家都非看不可的,而且那個時候開始講究電影院的音效,常常去電影院看國片的時候,前面預告啊很震撼,然後一開始播國片,好像整個氣勢小了一半的樣子,我們沒錢去做那些。所以就變成有兩個極端,要看娛樂片就去看好萊塢大片,要看藝術片、得獎的片,那時候金馬影展也推一段時間了,也是會去看國外的。如果是台灣的電影,就會覺得那我等錄影帶就好了,反正它的音效也沒有很好,小小感動的故事何必花那個錢。
有人說電影一定是商業行為,可是我覺得它的本質光是商業行為不足以概括的。因為我覺得整個社會的民主化、開放,會讓年輕人想拍的東西、創意上所關注的事情,會愈來愈不一樣,這是很重要的。
這一段時間,我感覺到想拍電影的年輕人還有一個出路,就是公共電視的「人生劇展」,它開放很大的空間給創作者。我記得那一段時間前後,我們一起組導演創作聯盟在衝撞的時候,也就是很想跟這些責怪導演的片商說,其實你不能只是罵導演拍片沒票房,電影的特效、演員的培養,都要不斷地下功夫去努力才行,而且電影公司也不敢投資,不是嗎?
那時候還好有「人生劇展」成為很多導演可以盡其在我發揮的地方,如果再加一點錢拍長一點,再出個拷貝,或許就可以變成一部電影(當時用這種製作模式操作的電影,製作費幾乎都在五百萬以內),我覺得大家就是此起彼落一直往前走。
(摘自《我們這樣拍電影》,大塊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王小棣
橫跨電影、電視,獲得金鐘獎最佳導演、最佳劇情片肯定,帶出很多年輕創作者和優秀演員。一九九五年執導第一部電影《飛天》,一九九七年推出台灣本土手繪的長篇劇情動畫《魔法阿媽》,二○○四年為兒童議題製作了電影《擁抱大白熊》。二○一四年獲得國家文藝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