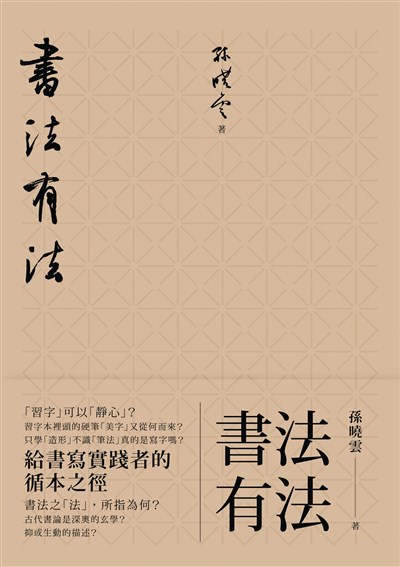 《書法有法》,典藏出版
圖/典藏出版社提供
《書法有法》,典藏出版
圖/典藏出版社提供
文/孫曉雲 圖/典藏出版社提供
書法的學習,與識字同步,只有一個途徑臨摹。回憶起來,我的困惑大都是從臨摹中產生的。
就今天來說,何止是碑帖,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磚文等,都在我們臨摹的範疇。這些文字幾乎都是以文字的載體質地而命名的。先來客觀地看看,這些文字質地的形成過程:
甲骨文:我們迄今為止見到中國最早的文字,是先用毛筆書丹於動物的骨頭上,再用利器單線刻出;為利於觀看,則須將字拓出。
金文:一種是用毛筆將字寫在模子上,刻好,再澆鑄金屬溶液;另一種是在已鑄好的金屬器上用毛筆寫字,再刻之,後人再拓出。
磚文:將字用毛筆寫於磚坯上,刻之,或直接刻於磚坯上,再入窯燒制;同樣須拓出。
碑文:主要指魏碑、漢碑;亦是首先用毛筆書寫於石碑,刻之,再拓出。
可見,以上文字的形成直觀,至少是需要三、四道工序才得以完成。經過鑿、刻、燒、鑄、拓,外加年久風蝕殘剝,毛筆的真實筆跡已完全喪失殆盡,它留給我們的,只是經過多次客觀「再創造」的大約的字形而已。
臨摹的目的
我們臨摹的最初目的是什麼?學習古人的用筆與造型。我們手裡用來臨摹的工具是什麼?毛筆、紙、墨。
試問,僅用毛筆、紙、墨臨寫,就想把那些經過多次「再創造」的痕跡表現出來,畢竟勉強,並由此揣摩古人當時的筆法真跡,實際上已無意間「指鹿為馬」。
這裡的「指鹿為馬」,正是蘇東坡《日喻》中瞎子以鐘、龠為太陽的意思。
比如甲骨文的兩頭尖的單線,完全是由於刻畫而成,根本就不是當時書寫的本來面目。同樣,金文的均勻圓光,漢碑的殘剝蒼茫,亦都不是其書寫的原來面目。我年輕時,當然也稀裡糊塗地臨過大篆金文、漢碑魏碑等幾乎所有書體,我疑慮叢叢,困惑驟生,內心從來沒有踏實過。
因為,我實在是看重毛筆蘸了墨,寫在紙上的必然結果。
早在宋代,米芾就指出:「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帖與真跡最近,所以臨摹主要臨真跡、閣帖,或刻工極逼真的碑,帖中雖然大有摹本,亦比揣摩大約的字形要準確得多。
若石刻是凡人、工人隨意書寫,加上粗制,雖然有它的天真、稚樸,但不能作為一種標準去取法,去崇拜。在「共性」尚未達標時,是沒有資格論「個性」的。正像一個人要滿十八歲,才能擁有成人的各項權利。
真正高貴的藝術,是千百年來人工精心培育的鮮花,而絕不是那些在路邊隨意飄曳的野草。
(摘自《書法有法》,典藏出版)
作者簡介
孫曉雲
女,一九五五年生於南京。三歲始,承家傳習書畫,曾在農村做知青五年、部隊服役八年。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江蘇省書法家協會主席,中國書協行書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院副院長,江蘇省文聯副主席,江蘇省美術館名譽館長。國家一級美術師,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書法作品曾八次獲全國書法大獎。先後由華藝出版社、台灣未來書城出版社(正體字版)、知識出版社、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美術出版社、日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日文版)出版理論專著《書法有法》,十五年暢銷不衰,先後十八次再版,創全中國書法理論書籍銷售量最高紀錄,並作為唯一書法理論書籍進入國家「農家書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