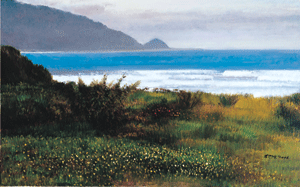 千年過去了,人間的起落和國家的興衰,在你的法眼裡,不過是一樹之距的飄程。可否在有生之年,讓平凡如我看見你的尊容,親口對我說,你看過無數的殞落與升起,最後留下的可有甚麼?
千年過去了,人間的起落和國家的興衰,在你的法眼裡,不過是一樹之距的飄程。可否在有生之年,讓平凡如我看見你的尊容,親口對我說,你看過無數的殞落與升起,最後留下的可有甚麼?
山一程,水一程,翼望在不再開合的眼睛裡,捕捉你的殘餘。你很機靈,察覺遠處有人在跟蹤,倏然化為一縷輕煙,走了。風一更,雪一更,回故鄉的夢裡,又尋見你在前方的山嶺,急遽奔向你,就在驀然回首之際,你吹口氣喚來雲駟,也走了。
透過身體的步履與呼吸,我從生命的初起,感受你的氣息,也從悼亡的哀慟裡,探聽你的來去。是否處於存在狀態,你就會在那裡。「人的命運有時並非操縱在自己手裡,生命奧妙,就要及時在生之時,好好來一場時空遊戲。」還是你透過先哲之口,提醒人們趁著還健在,不要蹉跎在生之時任她隨意消逝。
●
天地生成之前你已遊走於渾沌天際,而四季的運轉,春天的萌發、夏天的繁榮、秋天的蕭瑟、冬天的沉寂,也在你的陪隨下更迭時節的變換。因為無影無形,你不羈的身形早已輕飄在任何角落。無聲無息的你,從古至今的文化演轉,歷史巨流裡流竄過的每場擴疆展域的戰事,你也身在其中。是的,鄭和在海上與鄰國睦鄰斡旋的場面,你在那裡;亞歷山大的大軍困頓在印度的恆河時顯露的困頓,你也在窺笑。被處以宮刑的史學家司馬遷,他手中的筆飛舞急走時,你就在紙上解讀作者的心情。當詩人杜甫悲嘆著「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時,你也在轔轔聲不斷的車陣,見證古今人間綿延不斷的悲楚苦情。
上天下地都難不倒你,在號稱「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你站在喜馬拉雅山的頂峰,監看著眾河的第一瓢水,長江、黃河、湄公河、薩爾溫江、印度河、布拉馬普特拉河、塔里木河,是否順著既定的流向,為普羅大眾提供生命的能量。
你是虛無之神,屋瓦下的或水底下地裡的云云生靈,他們生理與心理的起伏動盪,你也等閒視之。紅塵的一切,在你飄渺的視界,如風般不停的遷徙;也似雲不歇的追尋。你所吟唱的是匿名卻永恆的傳說。
千年過去又千年過去了,人間的起落和國家的興衰,在你的法眼裡,不過是一樹之距的飄程。我只是凡人,有個卑微的請求,可否在有生之年,讓平凡如我看見你的尊容,親口對我說,你看過無數的殞落與升起,最後留下的可有甚麼?
●
我想,你不容許有人膽敢打擾你的平靜和神秘。在你的浩瀚領域,無論親情、愛情、友情或任何款情,全是一場又一場的記事。血流成河的慘景或孟姜女哭牆為夫的激烈,冷然的你或是無情無慾的你,於一切的點點滴滴,對待如風吹拂不見痕跡般稀鬆。 誰能怪你呢?你的個性是不會對名或利有絲毫的眷戀,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想聚就聚想散就散,這不是獨有的特權,凡是生物皆是如此,雖然惆悵,還是失望地眼見你踩著歲月的翅膀飛走了。
然而,我還是亟欲與你來一次生命的答辯。想跟上你的飄泊,我去找你的朋友們,可是他們學你出門了。有的走北京的紫禁城憑弔歷史的繁華與滄桑,有的登玉山山巔詠嘆天地之蒼茫。從書籍裡找尋智者的卓見,無論是孔子或蘇格拉底,他們的言語都太智慧太方正也太形而上。聖哲的話止不住裡的癢。
最後,宗教是絕望時能攀附的一根繩索。學你一樣,走進遙遠深廣的中國,九華山、峨嵋山、泰山、黃山等地的名寺古剎,這些聖地的每一塊石階都有我的卑微腳印。雖然仙道多險,路途霧大,決心一如負劍刺秦始皇的荊軻往前邁進。可是,佛祖只是慈祥地看著我,只默默告示我「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複未至」。不管,我要大聲地在天地間呼你喊你,加快腳步追你的背影。只要能夠找到你,我不怕走進虻虺當家的沼澤地,不退縮在鱷魚成群的疾流,不怕越過狼嗥虎嘯的山林。即便似遠古的夸父追日而倒,我也要找到你。
●
算了,我不想與你纏鬥,與你之間的糾葛將無止無休,屢戰屢敗,雖敗猶起,固然可以顯出人的一種尊嚴,一種悲壯,終究還是會敗北下來。
不要對我如此殘酷,在我停止喘息的當下,耳朵早已聽不到任何聲息,你卻得意地坐在我僵硬的身體,輕鬆說一聲「你錯過了」。不,我要辦一場觀落陰,呼求木匠魯班的魂魄,告訴我如何製作無色無形的暗釘,在沉默之牆,再請順風耳探聽萬里之外的輕音,千里眼的無邊眼力也會在無邊無際的四方找你,當你悄然出現之時,將你固定的牆面。
還能尋覓你多久?每天的日升月落,每起的風起雲湧,你來了也走了。當你來了,青鳥飛過,青鳥還在。當你走了,鐘聲遠去,鐘聲還在。請你告訴我,是否要微觀密照,心境要清澄明淨,才可以在記憶的河流裡,回想起你瞬間的美麗。
天空與大地依然遙遠,極目也走不盡前方蜿蜒的蒼茫。時間,有話對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