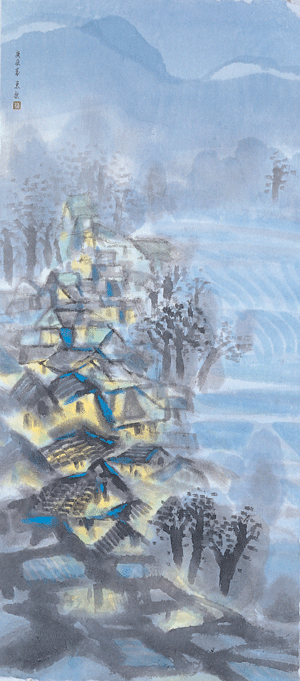
曉風月中的沾水垂柳,廂房內茶香的餘味,檀木桌上未境的書畫,自有一份燈深雨細的溫柔。而此刻雨橫風起,執槍守衛的戰士,依然昂揚挺立。
欲雨的天空,總似隱含不解心事的沉鬱。
稍一垂目凝思,再睜開眼時,夕陽已隱遁,天際盤據著不知何時聚攏的烏雲。不過瞬間,原本喧鬧溫馨的景象,立即轉化為淒清空寂。我凝神諦聽,林梢間吱喳嬉戲的鳥雀皆已歸巢,競相吹唱的夏蟬也噤口不語,僅有由遠而近的暮風,漸趨猛烈,吹得四野的蘆葦颯颯地顫抖。
我已在這裡站了很久。
久立不動的姿勢令我的雙腿酸麻,此種感覺自趾尖沿著小腿往上蔓延,像萬千千螞蟻的爬動,我竭力忍受,十餘分鐘後便毫無所覺。許多生活中的不適,或也是如此轉化為另一種型態的自立。我走出崗哨,崗哨旁是一列彎曲的石階,直通山頂,冷冽光滑的石階不知曾留下多少前人的足印。山頂有座無主的孤墳,初時頗為畏懼,久之倒也坦然,不過是微微隆起的土丘,和一塊傾斜的積苔長石而已。我沿著石階爬至坡頂,此地的視野遼闊,適宜遠眺,整個營區遂一覽無遺地展現在眼前。
營區的西南方環峙著綿延的山脈,山脈橫陳的姿態,無分晴雨,恆是千古的沉默。山勢雖不雄偉,但自有一份恬適閒淡的安然。由於缺乏水源,加以土質貧瘠,故而依著山勢墾拓的可耕地,僅能種些花生、蕃薯之類的雜糧。記得每次搭北迴線的火車時,也是同樣的景象,充滿了靜待的喜悅。
花蓮的山,祥和而溫雅地峙立,環抱著田疇綠野,彷若隨手可掬,是那麼親近,可以是家居生活中的一事一物;這些山川河海,就如父母於子女,我們之於國家,沒有熱血沸騰,雖清淡卻自有深摯的情意在。而火車轟隆轟隆地前行,海,似乎離得很遠,唯有訪若夢中的浪濤聲,隱約可聞。
山腳下圍牆邊,有口廢棄的水井,四周蔓生著約半人高的野草,井旁的水泥地猶遺有蘚苔乾涸的殘痕。仲夏以後的深夜,偶遇停水的日子,我們便三三兩兩至此洗澡。靜夜的蒼穹下,不知名姓的星辰在水面悄然遞移,蛙鳴蟲叫盈滿耳際,在月光的映照下,裸露的年輕軀體泛著微微的青光,飽滿結實的肌肉充溢著激昂的生命力。含帶細沙的井水一盆盆當頭淋下,冷冽自頭頂襲下,暖意則自腳底昇起。
正對著營區,是一道既高且長的土堤。碰上大雨滂沱,如有人撐著黑傘踽踽行過長堤 ,衣袂經風掀飄而起,那真是充滿了異國情調,是屬於詭異,淒寂的東洋風味。
素來對於島國狹隘陰淺的風情缺乏好感,我愛的是吾國紮根於大地的廣袤開闊,以及醞釀於山河的明朗自在。唯其如此,方能自滄桑中滋生新機,歷變亂仍不動搖,容天地萬物而不改其質。
大門右側,是內角國小。低矮的校舍,掩映在蔥翠油的綠樹叢中。土黃的跑道圈住小小的操場,跑道旁是舊輪胎製成的鞦韆。校園內遍植粗壯的榕樹,枯葉悠悠地堆積在土黃泥地上,榕樹長垂的鬚根每每在風中擺盪糾纏不清,彷如前世未了的宿怨,延至今生猶難化解。整體的校園有著悠遠沉緩的古意,除卻跋涉過久遠歲月的艱辛外,更蘊有現代化校園普遍欠缺的親和。晨間操課時,往往隨著山風飄來孩童稚嫩清亮的歌聲,和戰士雄偉豪邁的軍歌混在一起,一時之間,令人心生感動,望著東昇的旭日,心想,在新生一代的成長茁壯之際,也同時預見明日的希望。江山可待。
天色如漸次加濃的潑墨,愈來愈黯淡,我隱約看見遠處沙塵遍布,漸往四野擴散。初來時,頗為驚訝於此地的景致。晴天,陽光熾熱似火,稍有風吹草動,便是黃沙滾滾,彷如北國無垠的大漠荒野,駝頸間的銅鈴轉響,逐水草而居的漢家郎,這些都充滿了激昂的生命力,令人直想長嘯放馬奔馳而去;逢著落雨的日子,則又是截然不同的景觀,但見泥濘遍地,盡是積水,這該是南方寧靜沉鬱的沼澤吧?曉風殘月中的沾水垂柳,廂房內茶香的餘味,檀木桌上未竟的書畫,自有一份燈深雨細的溫柔。而此刻雨橫風起,執槍守衛的戰士,依然昂揚挺立。
風自窗縫鑽過,急促地呼呼作響,那種急促低沉的聲音,摻雜著似欲將人吞噬的孤寂。卓然傲立的群樹不改白日的姿態,唯有排水溝旁的楊柳,經過強風肆意地撫弄,盡失平時的優雅,此際,像極了披頭散髮的怨婦。待得風靜止時,聲悄人寂,只有隱隱傳來海潮般沙沙的迴響。
我從樹隙間望過去,不遠處,民房的燈火幽微地閃動,像盞浮懸在空中的紅燈籠。記得那個梅雨紛飛的暮春,我在嶺上受訓,每當夜半站衛兵時,總是怔忡地望著台中盆地燦爛的燈海出神,絲毫不覺夜露的寒涼。有時,一長串的燈嗚嗚地蜿蜒前行,心頭更是一酸,是火車,橫過盆地的上行夜車,可能載我回家?我感覺到孤獨極了,對於時空的感覺頓然錯落破碎如一地零散的光影。想到家人是否已安然入睡?想到北部山城的女孩,是否仍在燈下等候?梅雨時節滋生的青苔,是否已悄然爬上伊的窗前?想到遠在烏坵不愛說再見的友人,那兒可有翠綠的五葉樹?就讓其在風中頻頻搖手,代他道一聲珍重……。這樣死寂的夜晚,仍有奔波的旅人風塵僕僕未歇,省道上偶然疾駛而過的汽車,是大地唯一的脈動;我感到異常寥落,過往的一切皆在此時向我現身,驀然驚覺,自己依然軟弱如昔。
關於寂寞,似乎是件挺無聊的事。戍守的戰士寂寞嗎?眼睛鷹般地凝望遠處,握在手中是冷冷的步槍,發亮的刺刀。高峰絕頂上的氣象觀測員呢?身處高峰俯瞰人世,紀錄風向雨量,雲的舒卷,在氣象圖上預測明朝的晴雨,而降雪之後,這夜更漫長了。原始林區內的伐木工人呢?參天巨木覆住跳躍的青春,色澤艷麗的蕈菇藏於角落觀望,陽光在林外很遠的地方,啟動電鋸的剎那,心中可曾盤算,或許中秋霜降之後,可以下山一趟,離島的燈塔看守員又如何?繁華是很遙遠的事,濤聲永不止息,燈塔耀眼的光束,導引黯夜航行的船艦,不知能否照亮他的歸程?而海風擂鼓般地狂叩房門,寂寞則在窗外的黑夜裡窺伺。也許,歷史的巨浪中,個人一己的悲喜,不過是小小的微波漣漪;而諸如世事人情,總似沙灘與海浪重複千年的聚合般的無奈,只要曾竭力邁前,生活至此皆已無怨。
黑暗終於完全籠罩大地。昨夜忘了關窗,夜來風雨,幾度驚夢,清晨是被飄進室內的雨絲喚醒;而此刻彷彿雨已下盡,醞釀許久的烏雲盡散,露出銀盤似的月亮。晶燦的月光襯托下,這山的稜線忽隱忽現,飽含水意的霧氣自山腹間層湧而出,我感覺有風吹過,但仍毫無攔阻地疾掠而去,層湧的霧氣絲毫不覺著有絲毫的移動。風中漠然翻動葉片的相思樹,宛如走到盡頭的愛情,冷然無語。
不知何處傳來台語歌曲,隱約的歌聲哀訴命運的無奈,以及造化的弄人,身緊軍旅,總有隔絕人間煙火之感,只有在聽到一首歌,或接到一封信時,才恍然驚覺,是的,自己仍在人世,黃昏寂寞的風中,奔波人世的況味,深夜小巷的叫賣,湧上心頭的淒涼,這些都是不容抹煞的事實,在在顯示這個紛擾世界的溫暖與冷漠,美麗與醜陋,光明和黑暗;而時序運轉,既生為人,便得嚐盡千般滋味,在火獄自焚中企求新生。
我很累了,遠處傳來換班衛兵的腳步聲,是該回去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