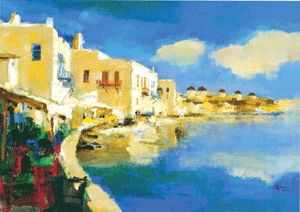
人和山基本上是一樣的,頭頂著天,根連著地,唯一不同的是人可以動,山不可以動,因為一動就麻煩了,這個道理長大後才懂,才知道地震來襲的夜裡,母親總是一次一次的呼喊,地牛不要動...
是人,沒有不想在這個塵世掙出一片天的,那怕是販夫走卒,也都有著那行業的一片天,於是,眼看著地,頭頂著天,人就在這天地之間努力掙扎著,死而後已,有些人或許得到了天空,但卻失去了大地,有些人則上下都落了空。
這一個生命掙扎的故事,我從小就聽過,初夏,住在南方島上的外祖父指著一個院落中樹上的繭說:「那是什麼啊!」,我說:「那是要變成蝴蝶的繭。」,從那天起,我要等待很長的夏天,才會等到蝴蝶破繭而出的時候,那種等待是焦慮又漫長的。有一次,我真的等不及要看到蝴蝶漂亮的色彩,於是偷偷的利用祖父不在的時候,用剪子在繭上剪了一個洞,第二天,我發現蝴蝶摔死在樹下,組父後來也知道了這件事,他沒有責怪我的魯莽,只是笑著對我說,所有堅強的生命都是來自不斷的掙扎,蝴蝶要脫繭而出之前必須努力運動,目的是使自己的翅膀有力飛翔,你以為幫了蝴蝶的忙,其實是害了它。
我一直記著這句話,讀小學時,島上正值白色恐怖的五○年代,祖父是知青,日據時代幫日本政府做過事,為了逃避搜捕,進入人煙罕至的山區躲了一年,靠狩獵維生才逃過劫難,後來棄文從農,高齡才過世,掙扎求生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生命的哲學。
五○年代的台灣,剛脫離日本統治不久,說一口流利日語的祖父開始學國語,幾位舅舅也才從日語學校的環境轉換成國語,一切都顯得剛剛開始,但是沒有人有怨言,因為在高壓的統治下,也沒有人敢再抱怨,祖父一邊學國語,一邊說:我們也是蝴蝶啊!努力掙扎吧。
雖然,白色恐怖的氣氛已經稍微緩和,但是,祖父仍然時時準備入山,睡覺時總把背包放在床枕頭邊,裡面有幾件衣服和幾本書,有一次,他帶著舅舅和我到山上,走了一天一夜的路才到達,一路上也少有人煙,來到一個山洞前,祖父說,這是我躲的地方,你們記得洞前這株老榕樹,還有前面這條小溪,進入洞裡只見著簡單的炊具,每天的食物幾乎都要靠打獵,不然就是野果,祖父是一位掙扎求生的高手。
那次登山是我第一次對台灣山區的印像,祖父說:山洞附近是原住民的地盤,所以最好不要亂走,我心中擔心在回途時會遇到他們,但是並沒有,後來我才知道原住民都是祖父的朋友,在白色恐怖時代,因為原住民的支助,祖父才能活著,這些原住民朋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下山找祖父,那時候,平地小孩很怕看到原住民,因為錯誤的教育印記把原住民朋友視為生蕃,下山的原住民會帶東西和祖父交換,我常躲在門後候偷看著他們臉上的刺青。我記得祖父是用日語和他們溝通的,他們臉上的刺青很迷人。
寒暑假的時候,我才能住在祖父家,才能接近屋後那座神祕的大山,所以,我一直希望放假的日子趕緊到來,除了假期,我必須回到城裡上課,那時很多教室都被兵占了,這些兵平常沒事會在學校的圍牆上用油漆寫著反攻大陸殺朱拔毛,我那時很奇怪他們為什麼都寫錯字,朱應該是豬才對,但是我都不敢說,那時,上課時要帶著自己的小椅子,躲在樹下,夏天還可以聽到知了的歌聲,冬天就是很大的虐待了,所以,我不喜歡學校。總是盼望著快回到鄉下。
城市的生活是很平淡的,卻從未想過那種平淡是戰時一直無法掌握的幸福,戰後第一代無法理解災難是什麼,而剛走過災難的父母也儘量不去回憶那段日子的辛酸,唯一的災難是八七水災,發生在五○年代的末尾,大水加上漲潮,把半個城市都淹沒了,我家在這個港市的高地區,所以未淹水,但是逃災的人把屋裡擠滿了,不少人只能睡在屋外的亭子腳,大水幾天未退,很高興不必上課,所以就把門板當作船筏,整天在水裡玩,自從那一次大水一直到九○年代,很少再發大水,卻沒想到台灣進入九○年代後,經濟生活改善了,但是發大水的災難卻不停的上演,懂事後才知道災難關連著人口的增加,土地的無止境開發,這種無止境的濫墾還關連著童年記憶中的那座山,那座曾經保護過祖父的山。
人和山基本上是一樣的,頭頂著天,根連著地,唯一不同的是人可以動,山不可以動,因為一動就麻煩了,這個道理長大後才懂,才知道地震來襲的夜裡,母親總是一次一次的呼喊,地牛不要動。
但是,山並未聽母親的話,在人力的因素下一動再動,等我成年有機會親近每一座大山時,才知道山已經變了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