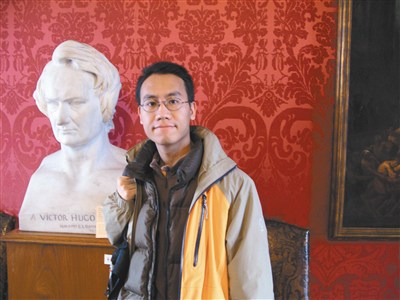 記憶後書 大阪來的畫
記憶後書 大阪來的畫
文/鄭政恆
關於大阪,我想起二○○七年的八月炎夏,登上天守閣,尋找谷崎潤一郎文學碑,在道頓崛看大蟹模型,在心齋橋的雅典書店買了森山大道的攝影集《遠野物語》,教了一課英文,寄居朋友的家,然後獨自出門,尋訪大大小小的電影院和潮流商店。也許在京都和奈良已看了不少文物,印象中沒有參觀大阪天王寺的博物館;又也許在博物館門前走過,還是沒有入內參觀。
走進香港藝術館,剛好有「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宋、元、明中國書畫珍品展」,可以補足當年無意的遺漏,反正看傳統國畫的人相對不多,只要靜心慢慢看總能引起內心的感應。
一些作品的畫家介紹前加上一個「傳」字,大概作品不是真蹟,而是後人所畫甚至假託。然而這些畫作尤其富於想像力,張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繪星宿眾神,王維的《伏生授經圖》想像儒生伏勝講經,他清枯瘦,但目光有神,只穿輕紗和抱腹,坐在蒲團上,右手執卷,漢朝的老教授好像有幾分疏狂,有從大學問而來的一分自信。李成與王曉的《讀碑窠石圖》,款題曰「王曉人物,李成樹石」,固有李成畫作獨有的蟹爪樹枝,加強了陰森的氣氛,右方有玄武馱碑,我們看不到巨型碑上的文字,執仗的僕從背對著窠石、樹木和碑石,唯獨畫中騎驢戴笠的白衣文人可以辨識了,也只有他一個人仔細讀碑,面對盛世或亂世時銘刻在上的歷史記憶。
流傳下來的珍品真蹟為數不少。我一邊走走看看,心裡想很久沒有看過這麼好看的展覽了。元代畫家的兩幅傑作特別耐得住仔細推敲,令我駐足不動,興許都是國破遺民的沉鬱之作,情感飽滿,卻下筆淡然,意象分明,但寄意深沉。
龔開的《瘦馬圖(駿骨圖)》令人立刻想起古道、西風、瘦馬,西風吹起了馬尾和鬃毛,最獨特是瘦馬身上的十五肋駿骨都相當清晰,龔開自題:「一從雲霧降天關,空盡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這本是一匹駿馬,有先天的驕人才具,當下卻是骨瘦如柴,眼神抑鬱,低首而行,無法一展所長,奔馳而往,確是遺民畫者的自況,也只有身歷劫難,才可如此寄意深長。
另一幅傑作是鄭思肖的《墨蘭圖》,還記得去年討論友人馬珠作品中的蘭花意象時,就以這幅《墨蘭圖》為例,想不到有機會看到真蹟。當時我說此作是「政治的蘭花,很枯淡,無根無土,寄託了外族統治下文人的一分悲情」,有多枯淡呢?當時只有一個概念。現在才看到畫者下筆非常簡潔,用墨少但功力深,至蘭花的尖端,墨色已是依稀,但尚有感情在,鄭思肖自題:「向來俯首問羲皇,汝是何人到此鄉。未有畫前開鼻孔,滿天浮動古馨香。」
問蘭足矣,聞蘭倒是不必,猶如讀屈賦的香草美人,人格的馨香從文字與筆墨,絲絲縷縷,浮動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