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眼的陽光從落地窗透光的角度篩進屋來,飾著青綠,並且飄揚著茉莉花香,我一襲寬大輕裝,斜躺在沙發,翻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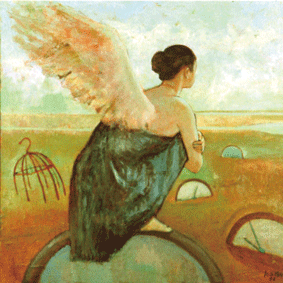 剛買回來的一本小說,讀到蕩氣迴腸之際,突然電鈴聲響起,一位久違的朋友未事先預告,突來造訪。
剛買回來的一本小說,讀到蕩氣迴腸之際,突然電鈴聲響起,一位久違的朋友未事先預告,突來造訪。
我記得很清楚,當天他穿著一件蓬鬆鬆的灰襯衫,鬍鬚未刮乾淨,鬍渣渣留了一小截,剛剛冒出頭來,頭髮微捲,雙眼浮腫,看來一夜未有好眠,甫坐定,淚已悄悄從瞇著眼的小細縫中滂沱滑落,溢出眼眶,垂下雙頰,把我新買的衛生紙硬生生用掉一疊,即使如是,依舊止不住心中的傷懷,我一邊安慰,一邊聽他泣訴從前。
太陽光烈得很不真實,我們被烤曝得渾身不自在,我起身將帘子拉上,泡上一壺剛剛購自新竹的東方美人,這是一款我不熟悉的茶飲,但濃郁有味,友人愛極了,哭裡帶笑,頻頻說讚。
之後,空氣彷彿凝結一般,靜靜流逝,他若有所思,不作一語,一口接一口啜飲著茶,我陪他坐著,等待他繼續訴說。
「最近常常去看媽媽。」
他的話讓我覺得突兀,如果沒有記錯,他的媽媽兩年前已作古,不可能傾聽他的心事?
他未等我提問,彷彿知道疑惑一般,指明是在墓前,兀自站著,把心中藏著的千絲萬縷講了一遍又一遍,他嘴角囁嚅著,溜出一些不太清晰的話,彷彿余光中的詩,他想我,我忘了想他,我想他,他再也無法想我了,我聽得感動,以至於心跟著一起緩緩抽動。
是的,心情真像余光中,他的詩膾炙人口,詩集我本本喜歡,有如收藏家在書架開來,且能如數家珍般的吟誦,尤愛《鄉愁》,每每行走野徑,獨坐幽篁裡,經常不由自主的想起它:
小時候,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
後來啊,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
母親在裡頭。
……
讀著、讀著,心一揪,漫漶的眼淚盈出眼眶,迷散開來,文中訴及母親的那段文字,很容易把人引入了懷思之中。
朋友的心事,一度也是我的哀愁,結結實實遺忘一件人間事,忽略每個人都會老,而父母絕對比我先老,因而沒能保握住交錯的分分秒秒,瞬間剎那,往往就更來不及了,上演子欲養卻親不在的窘境。
人何以如是?
我不得而知。
縱放幸福彷彿成了一種理所當然,我們忘記用角色互換的心情思考,連我自己都是這些年,禁不起時間的淘洗,才明白父母當年的內心世界,媽媽從口中重複傳送出來的吱吱聲,原來是腳關節摩擦疼痛的吶喊,啊啊啊則是風濕痛的告解,呼呼呼應該是上氣接不了下氣的控訴吧,我未及老時的確難以知曉,因為從未有人預告,老了之後會幻化成這樣的容貌?
友人最痛之處,當媽媽需要他有耐心之時,他卻多了怨言,需要有人扶持時,他只是放手讓瑪麗亞協助,她的大小便失禁,房間有異味,他只顧著一味嫌棄。
此際,他更加涕泗縱橫了,講述以前自己年紀小時,媽媽如何無怨的把飯菜大口的放進口腔咀嚼成似泥的飯,小心翼翼的放進孩子口中;而當媽媽老到無法自己,牙齒鬆動時,他何以不能如法泡製,替她準備一份合宜的餐點?
朋友說,媽媽無怨無悔的更換紙尿布,有一天,她需要時,卻躲得遠遠的,最後他輕嘆一聲,淚眼潰堤,珠兒再度滑了下來。
我犯過同樣的錯,一度以為父親是個冷淡的人,沒有什麼情感,根本不理子女,怎知在他仙逝多年之後,我一點一滴拼湊,意外理解那是一張愛的地圖。證明他的愛很濃,澄澈純正,百之百金的,24K的,沒有矇混,只是換了一種形式,隱而不彰,不著痕跡的,幽幽淡淡呈現出來,誰理得一個大男人,晚上起身替我們蓋被,疼惜地在臉上輕輕拍了幾下,誰明白,他嗜吃魚頭,原來是把好吃有肉的魚身留給子女,這些事在我當了父親,方才明白那是愛,我開始承襲這樣的風格,像一條垃圾魚,撿吃兒女剩下的飯菜。
這些早逝的記憶,印象已經矇矇矓矓,有些糊了,卻因為一個感傷的朋友來訪,像湧泉一樣奔騰出來,久久不散。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