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朋友G的標準去度量,滿街都是值得同情的人。有的是物質上的,有的精神面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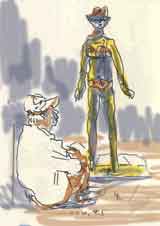
有一回聽G說出她的感受,很讓我覺得自己實在達不到。
「一個青年跑來對我講:從嘉義北上來看望母親不著,而今又沒了回去的盤纏,求我施捨。」G當即給了他錢。G說:「有人說,這人可能騙你的。當然那行徑的模式或極可能歸於騙,我也明白。但是我的信念是:如非不得已,他何至於說謊?」G的同情,出於人們之有「不得已」。
像這類時或在周邊出現的小騙局而言,我們首先因識破其騙之惡,同情即無從發生。而不能遠推至根源性的「人們不得已」的苦境。
G常常由小小善行獲致良好的自我感覺,而享受愉悅心情。譬如:見一婆婆顫巍巍行走在街廊,接著要穿越馬路的時候,G便上前攜扶,口說:「我也正要過街」,然後一直護送婆婆到對街一家便利商店進了門為止。
任務達成了,折返斑馬線,回到原先等公車的站牌,公車剛好抵達,快樂登車,不需曬太陽等待,一切恰恰好!
G的行為、觀點時遭挑戰,或有人說:「那婆婆買完東西從便利商店出來呢?之後的之後呢?」
G說:「我做自己所觸及和能力可以做到的事。往後則待新的機緣,不屬我念想之事了。」
都市街頭若公然行乞,係屬違警,於是出現一種新形式:手上多少拿點「商品」———原子筆啦,面紙等等,形狀一見便是博取同情者:衣著異樣,或懷中抱一孩子。而「商品」的開價超過所值甚大。
「忠孝復興捷運出口,常有一位瘦小的婆婆蹲著,推車籃裡放著的蔬菜,成色往往很糟的東西。」G說:「她也不兜售,只等路人發現她。有時熬到很晚,竟而瞌睡著了……」
「有一回,我從她推車籃裡看到一些樣子已不好的番茄,婆婆說:『一袋一百五。』實在貴得離譜,但我還是決定買她的。婆婆見我掏錢,趕緊補上一句:『兩袋算你三百啦』——本來就是三百嘛,想了想,還是拿了兩袋,實在是為了讓婆婆能早點回家。
但她見我拿出的紙鈔是五百元時,便說:『三袋算你五百啦,免找!』一方面我家裡吃不了這麼許多,一方面帶的錢有限,待會兒還要買別的東西,所以還是請婆婆找錢。
我拿著兩袋番茄及找回的二百元,才轉身離開,就聽到婆婆在身後尖聲叫喊:『喂!小姐!』———說我剛才的五百元並未付給她。我確實付了,請她再仔細找找。但婆婆又喊:『喂!小姐!沒有啦!』這樣再三的把我叫回。最後,我只好一股腦兒把兩袋番茄連同她找的二百元一起還了給她!」
值得欽佩的是,經過這種種的事,G的初心始終不改。
(本專欄隔周三刊出)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