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的沙漠,像黃色的精靈在逗引著我,數月前,當我一踏上台灣的土地時,懷念即刻開始。回想那一片無人的天地,藍天與黃沙,單單純純的二種色彩,養著單單純純的人類以及牛羊,還有我幾天內什麼都不想的腦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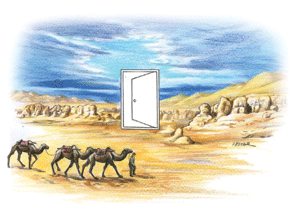 從櫥窗中望去,黑色、咖啡、白、紅、黃、粉紅、淺灰的鞋子,以及不再以純白吸引人們視覺的七彩花邊。稀有的白鞋,已漸漸從鞋架上消失。架上衣服,是各種顏色或是叫不出顏色的混色混調,只要能刺激眼瞳,裝點門面,讓消費者掏出購買慾及行動力,任何色調都是爭強鬥勝的色彩,足以在消費的部門攻佔領地,宣告存在的空間。
從櫥窗中望去,黑色、咖啡、白、紅、黃、粉紅、淺灰的鞋子,以及不再以純白吸引人們視覺的七彩花邊。稀有的白鞋,已漸漸從鞋架上消失。架上衣服,是各種顏色或是叫不出顏色的混色混調,只要能刺激眼瞳,裝點門面,讓消費者掏出購買慾及行動力,任何色調都是爭強鬥勝的色彩,足以在消費的部門攻佔領地,宣告存在的空間。
站在十字街頭,除了紅停綠行的燈光喚起我一點點的知覺之外,我似乎迷失在這個百色紛亂的花綠世界,這個看起來本是屬於我而今卻讓我迷惑的世界。
我的眼睛從黃沙中歸來,卻一時無法適應這樣的色彩。從無人的沙漠邊緣走出來,線條本是簡樸單一,卻突然在城市街頭畫成無數曲線、直線、斜線、彎線,我的心停留在沙塵僕僕的取經路途上。
昨夜西風起,屬金,肅殺之氣把秋天點染成悲傷的始祖。今晨,忽從西北方吹來第一道冷鋒,我拉起領口,穿上長袖外套,很難想起數月前,我在攝氏三、四十度的高昌故國,被瘦弱的驢馱著,在黃沙中一步一步走入黃沙。還有站在一陣熱風吹來便感到十分清涼的火燄山下,再也想不起來,熱與冷的對比是如何的清晰,甚至懷疑我曾夢過,那種情景曾經是唐僧走過的年代,是許多戰亂瀕仍,許多百年前繁榮的國度,百年過後即成廢墟,剩下幾塊土堆的故國遺趾。昔日高昌國盛極一時的講經大院,國王、貴族、許多熱愛佛法的達官顯要,聚集在同一座院落,或坐或站,恭敬地在如今僅剩半片圓牆的講經堂前,聆聽玄奘大師講經。一句接著一句的佛法從高僧口中吞吐,從耳入,存於心,澆灌著心中善法的種子,結下佛法諸法緣,然後,人們卻在時空急速流轉下,老去死去,一縷清靈飄向世界各地,像種子般掉落,重新生老病死,輪轉再三。高昌滅亡,數百年來,成為一堆一疊的黃土,唐僧不在,聽講的人們不在,繁榮之國已亡。
誰知後來,所有的緣分究竟飄至何處?昔日相聚之情,緣份從何而生,今日分散之處,又是何日再相逢?
緣起緣滅,誰知自己之善緣與惡緣?誰又明白這天地之間的變化到底在演示什麼道理?經過歲月之手,記憶已經分散,不再清楚當時的景象當時的人,只是眼前的許多生存問題引領著我們一直往前行去,忘記過去許下的願望,過去曾經愛過的人曾經聽聞的善法。
就像我現在站在二十一世紀的街頭,我何曾明白自己的過去,自己的未來?或許記憶止於三個月前的黃沙滾滾,我曾體驗了取經的艱苦,身體力行去閱讀那份時時刻刻與死亡交戰的記錄,也曾到達西安的大雁塔,同享唐僧歸國的榮耀光彩,然後,此刻,我卻在數千公里外的台灣,回想那一切,在腦海中被美化的記憶,以及阿賴耶識中被層層刻下的傷痕、歷史、愛恨、歡喜與悲傷。
那又是什麼呢?昔日聽聞的善法是否發芽呢?昔日的人們是否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尋找過去累世中淺淺的善緣?在如網羅般罩頂的忙碌裏,匆匆而來急急而去的神情已經寫著現代人的新生活,數百年前的小國之影,又何曾在內心停留?或許偶爾在燈紅酒綠之際,在黑鞋白襪的單色調中,望望藍天,會有一點莫名的感動,想要喚起內心的聲音,卻有些許聽不見回應的恐慌與淡淡的心酸吧!
我開始想念藍天與黃沙,兩種色調的世界,無人,純景。天地與人的對話無需修飾,甚至你一高興,可以與黃沙或是牧草講一整天的話,憤怒、悲傷、不平、歡喜、快樂都會化成一道塵沙,融入日出與日落的交會之間。特別是當我匆匆步行出門,半快步地跑完一天行程,或者是混戰一日的舌鋒想望著無語的時分時,這種渴望便油然昇起,渴望單純的生活、簡單的心境、清靈的心眼,讓我在這個多混多色彩的現代社會中,走在複雜的城市街道中,能夠簡單地取擇一條色調簡單,清楚明白的回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