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天葬,內心的失落其實遠大於觀看時帶來的強烈震撼,一時之間頗有人生虛幻之感,深覺人世一遭頓時恍若一場夢,來去之間什麼也留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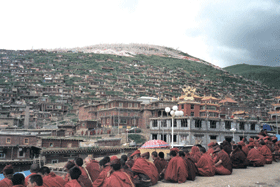
色達,位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東北部,境內地貌複雜,屬典型的川西地槽系巴顏喀拉山褶皺帶,有著草原、湖泊、河流……等特殊的地表,平均海拔在四千公尺以上,日照充足,屬高原季風性氣候,年均溫在零下一度左右,長冬無夏。色達在藏語裡是「金馬」的意思,傳說在那片富饒美麗的草原上曾發現過馬頭型的金子而得名,也有人說是因為在地下埋藏著一匹金馬。
此處草原繁密、牛羊眾多,從有形的建築到無形的氣味莫不充滿濃郁的藏式風情,然而最吸引人的莫過於馳名中外的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這是世界上最大的藏傳佛學院,它是晉美彭措法王於一九八○年為振興佛法、廣利有情所創建的學院,院內課程分為顯宗和密宗兩大部分,顯宗開設的課程有戒律、因明、俱舍、中觀、般若五大類,顯宗是日後修習密宗的基礎,各科修完一般大約要四、五年的時間,經過嚴格答辯及當眾辯論通過者,方能得到「法師」的稱號,才能為他人講經說法,其講求次第嚴謹及修學系統性的特點尤其突出,因此有許多來自四方的信眾紛沓而來投師學法。
在七月中旬燥熱不堪的天氣裡,我們從丹巴的黨嶺準備前往色達佛學院,然而丹巴並無長途客車直達,必須先到爐霍縣城轉搭過路車,幸喜下午三點半順利搭到從馬爾康發來的過路車,從爐霍轉三一八國道經色爾壩草原,約一百多公里即可抵達距離色達縣城二十多里處的喇榮溝,往山上直走就可抵達佛學院的所在地。
整個佛學院裡唯一的水源在半山間,闢為一個水泥平台,有十餘個出水口,看見不少僧尼背著盛接好的水,揹往自己簡陋的住所,有的僧尼則在平台上刷洗自己的衣服、被單,晚起的我們到半山平台漱洗時只見所有的僧尼已做完早課歸來。吃完早飯後,只見好幾輛車子上負載著用麻袋裹住的往生者,到此處請寺僧唸經超度,家境好的甚至請了數百僧眾齊聲為往生者誦經祈福,誦經完畢在山的另一邊將有天葬。
如果沒有來過佛學院的人,進山門後勢必會被連綿數公里布滿山谷的無數小木棚屋所震攝,其龐大的陣勢往往令人驚嘆得目瞪口呆,那些密密麻麻的簡單棚子是成千上萬僧尼的僧舍,據說這裡常住的僧尼高達二萬餘人,遇有佛事活動時人數甚至多至四萬人。雖然,整個佛學院裡的寺廟和佛堂規模都不很大,但裝飾布置卻十分考究和輝煌,不論是在任何一個角落,都可看到身披漿紅色僧袍的僧人在忙碌著,那種在極簡的環境中追求精神的信仰與靈魂的安頓的氛圍,一時之間令人不知自己究或在天堂抑或在人間,或者,它是在天堂與人間之外的另一個我們無法求索的世界。
基於對天葬儀式的好奇,午後三點我們包了一輛麵包車到山後的天葬台,車子僅能停在半山腰上,喘著氣隨著人群快步來到山上的凹谷,靜坐在草皮上觀看天葬台上的一切,只見天葬師手中拿了一斧一刀,台上有大約十具屍身等待處理,四週的山頭上已聚集了數百隻禿鷲,而三三兩兩盤聚在重要位置觀看這場盛會的是來自四方的遊客。一些拿著單眼相機、膽子大的旅人,他們無懼於濃烈的屍臭味,戴著簡易口罩就著天葬師處理屍首的每個程序猛按快門,當所有的禿鷲為啄食屍肉,自山稜線群起飛奔天葬台的壯觀場面,更是令人震懾!在短暫的時間內,所有的屍身皆被啄食乾淨,獨留幾隻烏鴉侍機而動,準備搶食地上殘留的肉屑。天葬師相中了一個往生者美白的頭顱,像雕刻藝術品一般,在所有人面前剔去附著在上面的血肉,這個舉動吸引了幾個法師的圍觀,大膽的旅人更是近距離地拍攝這難得一見的畫面。看完天葬,內心的失落其實遠大於觀看時帶來的強烈震撼,一時之間頗有人生虛幻之感,深覺人世一遭頓時恍若一場夢,來去之間什麼也留不住。
夜間的佛學院整個沉靜下來,所有僧尼回到各自的居所,那些低矮而簡陋的僧舍隨著天色漸晚而點上幽微的燈光,習慣繁華富裕生活的我們初來乍到,簡直為這些僧尼的困苦生活感到驚怖,然而卻有這麼多的僧尼選擇在此地做為他們修行佛法的所在,而且幾乎都做了長久居住的打算。深夜時分從最高處往下望,那種清新冷冽的空氣、極度清簡的日常生活,和它所散發出來的氛圍氣味,讓人深覺整個佛學院彷若完全靜置於時空之外,就像眼前所見的景象--在一片幽暗漆黑的寂靜山城中,沒有半點人聲車聲,唯見兩排昏黃的路燈,從最高處的建築一路逶迤到山門,然而你又清楚地知道有二萬多名僧尼置身其中。
每天早上,山上的最高建築物--壇城,它的上半部是轉經的地方,這裡總是聚集了無數的僧尼與藏人,人人手持轉經筒順時針繞行,據說若是身患疾病,只要在此轉上一百圈即可痊癒;它的下層是固定的轉經筒,金色的圓筒經歷過無數人的手漬而變得晶亮,而每個經筒轉動時所發出來的悠長的聲音,彷如一直從未停歇地嘎吱作響。天未亮就有虔誠的信徒,從山下陸續上山聚集壇城轉經,雖然我們也隨著人潮圍著轉經祈福,然而自己深知心中的感覺十分虛空,畢竟沒有如藏人一般強烈的宗教信仰,在神祗的面前更是不敢祈求任何。
第三天清晨我們即將離開,六點鐘打理好行裝,出門時天色仍黑,在微雨中打著手電筒摸黑下山,已有一些早起的僧人往壇城的方向前進,他們絕大多數保持沉默,但步伐卻是輕快而愉悅的。對困窘物質生活的不以為意、對佛學院以外的世界絕少關注,專心於佛法修行並且從中獲得絕大的精神慰藉,是整個佛學院散布出來的氣息,那種精神上的堅定與充實,比起表面富足的台灣人,真是強多了。再回首,看著密布於群山的僧舍,與山谷間隨風飄揚的五色經幡,我心中想著:再見了,色達,這一輩子再也不會來這裡,因為這樣強烈的行旅印象,一生一次已經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