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篆刻家鄧石如曾說過:「字畫疏處可使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這方印的美學表現,可以說是上述觀念的創作體現,是我一反常態的作品,並有段刻骨銘心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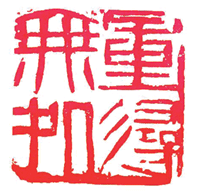
首先,改變平正的章法結構使其「不安」。針對印章邊線而言,右下邊寬線,左上邊無線,這種對等線的去邊與留邊是相互呼應的,如西洋攝影之「高反差處理」(非黑即白),按中國的說法是「留白」,所謂的虛實相生。
其次,印文的內容有疏有密,如「重」、「尋」二字是密;「無」、「處」二者是疏。密則不透風,甚至於不容針隙,疏處是無邊,比寬闊更甚,可達無盡。
再者,字體點畫是採離合、收放、明晦、輕重和起伏有致的對比變化,使印面豐富奇趣橫生。
這方印在刀法上的運用,亦改變往常精雕細琢的慢刀習慣,左手握石,右手執刀,以刀代筆,徒手猛力鑿刻,落刀如落筆,刀下石崩,不再補筆,這種單刀直入的方式,在當下頗能憾動自己。由於過度專心,多次被刻刀劃破手指,仍欲罷不能,完成後才驚覺血流如注,深雖不見骨但也銘記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