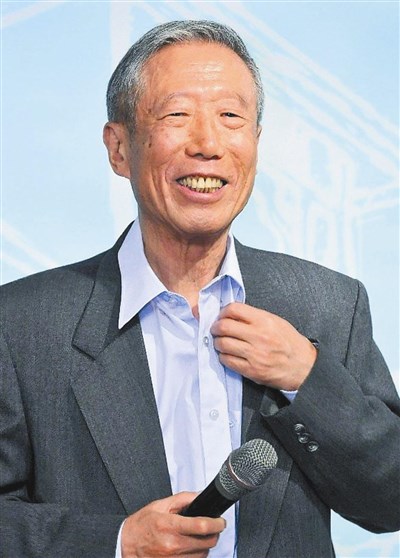 張作錦
圖/資料照片
張作錦
圖/資料照片
少年時期在大陸,隨家人去寺廟禮佛,通常要跋涉於深山叢林之間,因為寺廟多建築在那些地方。但是要去基督教堂,可就方便得多,因為都設在通衢大道、人煙稠密之處。
基督教標榜「神愛世人」,自然要主動去找「世人」。可是佛教的中心教義,不也是「普度眾生」嗎?為什麼不與「眾生」方便,反而為難他們呢?
到了台灣,星雲大師建佛光山,提倡「人間佛教」,乃使局面改觀。談人間,自然要入世,要近人,所以佛光山的道場,多在城鎮鬧區,以方便信眾禮佛、聽道、參加各種活動。星雲大師也一反宗教常有的門戶之見,他與基督教及其他宗教領袖多有往來。他創辦的《人間福報》,不是只刊載佛教的活動,各種宗教的消息都有。
這使我想起一則故事,根據西漢《說苑》記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焉何求?」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但是後人又找到一篇文章,老子也出來講話了:老耳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耳則至公也。
老耳話的出處為何,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的境界。楚共王的「楚弓楚得」是國家觀,孔子的「何必楚也」是世界觀,老子的「去其人」則是宇宙觀了。
我們現在有「人」,有「人間」,才可望更向上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