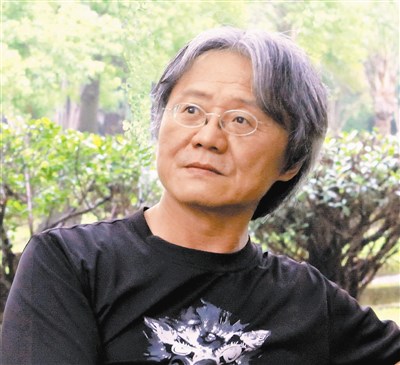 執筆人:路寒袖 作家
執筆人:路寒袖 作家
執筆人:路寒袖 作家
「村墟疏落認新城,平野荒蕪接太清。細草常緣官堠長,閒花多傍女牆生。月明尚少樓台影,日暮初添鼓角聲。父老衣冠存太樸,大成殿畔事春耕。」這是櫟社發起人之一、神岡大夫第後代呂敦禮的詩作,題為〈大墩新建府城〉,描繪出台灣府城—台中百年前的景致。透過這首古詩,我們看見了一八九○年代的台中,城樓雉堞、平疇綠野以及男耕女織、民風純良的和諧景象。
提到「府城」,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以為就是專指古都台南,殊不知,台中也曾貴為「台灣府城」,只是時日太短,早已化為歷史雲煙,難再追尋了。
為了喚醒這一段城市記憶,台中市文化局舉辦的「二○一六光影藝術節」即以台中建城故事的「城中城」為主題,考證出八座城門舊址,在該處以光影呈現城門意象。另外,也找出了台中的第一條街(舊大墩街),請藝術家沿途規畫各式裝置藝術,並舉辦導覽,讓市民如「哆啦A夢」般,搭著時光機,穿梭歷史時空,想像清代台灣省城的虛擬圖像,重新覓尋這座百年城市的發展軌跡。
追尋台中府城命運,要從「橋孜圖」這個密碼切入。
話說一八七四年,日本以漁民遭排灣族原住民殺害為由,進軍屏東車城,掀起牡丹社事件。此一事件,戳醒清國睡獅的麻木神經,開始著手海外的防務,正視兵險問題,福建巡撫岑毓英(轄區包括台灣)也思考將行政中心由台南遷移至彰化(亦即大台中),並且相中貓霧捒、烏日莊、上橋頭、下橋頭等風水寶地。
一八八五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規畫新的省城,一八八九年八月,正式動工興建,在東大墩街南側的新省城—橋孜圖(台語「橋仔頭」的雅化,位在今台中南區,國光路到台中路之間)附近興建城廓及衙署廟府。
橋孜圖新省城總面積約三點六平方公里,實際築城範圍在東大墩、頂橋仔、新庄仔一帶,工程規畫為八門四樓(八門:震威門、兌悅門、離照門、坎孚門、 艮安門、坤順門、巽正門、乾健門。四樓:朝陽樓、聽濤樓、鎮平樓、明遠樓)的八卦城池,總預算約為九十萬兩。
這是歷史給台中的第一次機會!眼見橋孜圖要躍上台灣政治舞台了,可惜「三年官,兩年滿」,巡撫劉銘傳積極建樹,一朝下台,人去政息,雖然建城已大興土木,完成第一期工程,但接任的邵友濂卻拒絕埋單,以財政不堪負荷為由,於一八九四年二月,奏請建城計畫終止,省城移設台北。「台中府城」粉墨一半未及出場,已曲終幕落。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馬關割讓,日本據台,一九○三年,日本推行市區改正計畫,台中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之城,由總督府衛生工程顧問巴頓(W.K. Barton)擘畫街區大重畫,仿造日本小京都格局,以火車站為起點,規畫台中成為棋盤狀的都市,並整治綠川、柳川、梅川,城區到處水流漫漫、綠柳垂楊,加上一九二○年代台灣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台中成為台灣最現代、最美麗的文化城市。這是歷史給予台中的第二次機會。
二戰結束,日本撤退,終結殖民統治,台中卻因新政權過客式治理及重北輕南政策,停滯空轉,競爭力盡失,讓台北市穩坐台灣頭。
歷史曾給予台中機會,歸納來說,前兩次都是「侍從主義(clientelism)」的垂直恩庇關係,權力掌握在統治者手裡,百姓無權決定自己城市的命運。但是,歷史並非冷酷無情,這次又給了台中機會。二○一○年底,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彷彿倚天屠龍刀劍合體,新台中有了新條件與新能量,所有失落的政治、經濟、交通、教育、文化的歷史拼圖,一夕之間全拼齊了。
與前兩次不一樣的是,歷經多次民主抗爭,挑戰專制,此時此刻,人民已然當家作主,徹底擺脫了「侍從主義」的枷鎖,這是歷史給台中的第三次機會,二七五萬的市民可要握住這難得的城市發展之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