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東渡
自北宋起,在福建「甌寧之水吉縣」(《福建通志》)製造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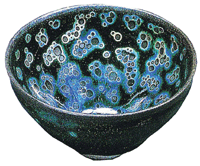 釉、厚胎的茶碗──建盞。窯址在今日建陽縣水吉鎮。
釉、厚胎的茶碗──建盞。窯址在今日建陽縣水吉鎮。
宋代之飲茶嗜好,上自皇帝,下及老百姓,十分普及。宋徽宗 認為飲茶活動具有:「沖澹、簡潔、高尚、雅靜之韻致」,是值得大力提倡的「高雅之趣味。」由於宋徽宗的崇高文化素養,他認為「點茶」(泡茶)宜選純白、青白,灰白、黃白則次之,深黑的「建盞」便成為絕配,在茶器之中,可與北宋官窯、龍泉窯的茶器媲美。但依程大昌的《演繁錄》記載,南宋皇帝御前賜榮已不用建盞。相對的,這些粗獷的茶碗反而普及於民間。
認為飲茶活動具有:「沖澹、簡潔、高尚、雅靜之韻致」,是值得大力提倡的「高雅之趣味。」由於宋徽宗的崇高文化素養,他認為「點茶」(泡茶)宜選純白、青白,灰白、黃白則次之,深黑的「建盞」便成為絕配,在茶器之中,可與北宋官窯、龍泉窯的茶器媲美。但依程大昌的《演繁錄》記載,南宋皇帝御前賜榮已不用建盞。相對的,這些粗獷的茶碗反而普及於民間。
元代以後為何停止製作建盞,並不十分清楚。從北宋到元初,建盞由興而衰;甚至故宮博物院也沒有收藏品。
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建盞於南宋東傳日本,十四世紀起即有官方記錄,自此以後,日人十分喜愛,數百年間未曾中斷,如今更有三件建盞被指定為「國寶」。
曜變建盞
蘇軾的〈送南屏謙師〉詩句如此:「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勿驚午盞兔毛斑,打出春甕鵝兒酒。」蔡褒的〈試茶〉也有類似詩句:「兔毫紫甌新,蟹眼清泉酒。雪凍作成花,雲開未垂縷。」楊萬里的〈以六一泉煮雙井茶〉又有「松風鳴雪兔毫霜」一句
詩人蘇軾的「兔毛斑」和蔡褒的「兔毫」及楊萬里的「兔毫」全部是指「兔毫盞」,即建盞的一種。
除了「兔毫」以外,建盞還有「油滴」,以及讓日本人為之瘋狂的「曜變」(或窯變)。「窯變」顧名思義,是燒製中的變化。令人感到驚奇的是,日本美術館藏品中有兩個「窯變」建盞的花樣十分接近,色彩燦爛,鮮艷奪目;同類建盞在中國卻一個也沒有。
日人珍愛
隨著榮西和尚在日本推廣飲茶,茶器成為飲茶必需品。宋、元之間的中、日商品,茶器成為搶手貨。一五七七年(明萬曆五年)的《御茶道具目錄》記錄了京都附近重要茶器收藏情形。建盞東渡日本,很快出現了喜好者,尤其是受到統治者的青睞,演變成一頁精采的文化傳播史。一四○八年的《北山殿行幸記》(足利義持將軍)、一四六七年的《君台觀左右帳記》(足利義政將軍)兩種史料都出現了兩位將軍收藏建盞的記錄。
在日本由於茶道的風行和在位者的提倡,建盞成為身價不凡的茶器,而中國在元末即不再生產,建盞已是可遇不可求的稀世珍品。這種情形,在民末清初大量文物外流後,日人才有機會重新目睹建盞風采。
建盞又稱天目碗
十分有趣的是,福建的黑釉茶碗,雖然曾經是朝廷貢品(碗底刻「供御」兩字),也曾經受到文人墨客的讚美;不久就衰微了。但流傳到東鄰的日本,數百年來,一直被鍾愛著,捧如天星。
建盞東渡異域後,被稱為「天目碗」。這個歷史上的誤傳,卻已成為日本固定稱呼。目前日本政府指定的三個「國寶」建盞,分別是「曜變天目茶碗」(兩個)和「油滴天目茶碗」(一個)。
而「建盞」之被稱為「天目」,由來已久。一三三五年日本登記寺院公物文獻中即出現「天目盞」的稱呼。茶道中的點茶也有「天目點」一詞。
「天目」的來源,乃是南宋的日本僧侶到中國時,多前往杭州附近的徑山、天目山修行,其中高僧圓爾辨圓更將禪法、茶經攜回日本。雖然目前沒有更可靠的證據可說明返回日本的佛教僧侶是從天目山帶回建盞,但因為浙江「天目山」的存在,使日本人把福建建陽燒製的黑釉茶碗稱之為「天目碗」。
三個國寶天目碗
被日本人拱為至寶的「天目碗」(建盞),目前公開於世的有三個「國寶」:
1.東京靜嘉堂文庫所藏:「曜變天目茶碗」
2.大阪藤田美術館所藏:「曜變天目茶碗」
3.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所藏:「油滴天目茶碗」
藤田美術館藏品由醫商「藤田組」創業者藤田傳三郎家人捐出。這個天目碗於一九一八年向將軍德川家直系傳人的水戶領主後人購得。
靜嘉堂文庫乃是三菱財團的附設美術館兼圖書館,所藏天目碗約於一九二○年買入。這個天目碗推測是幕府將軍足利家傳世茶器,戰國時期流入織田信長家。織田敗仗後,由部下送給後來統一天下的德川家康。家康之孫德川家光送給奶媽(春日局),又輾轉流入領主稻葉家。正因為如此,這個茶碗又被稱為「稻葉天目」。
另一個「天目碗」(東洋陶瓷美術館所藏)曾經是豐臣秀吉所擁有,後輾轉傳至京都西本願寺,三井財團、領主酒井家……其間也有精采的曲折情節。
中國的建盞,亦即日本的「天目碗」,經歷數百年,流傳了妙筆難以描述的故事。尤其是,「曜變」(窯變)有兩個出現在日本,中國竟不獲一見,實令人為之扼腕喟嘆!至於日本企業家之積極投入文化保護行列,也實在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