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已維持一段長時間,原先只是為了試圖由釋迦牟尼佛三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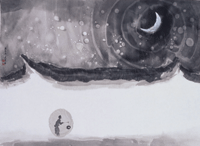 十二部言教中,了解佛教的義理及哲學意函。一部一部讀下來,原先的意圖已被顛覆,反而在讀經的過程中,與「字」進行深刻的接觸。
十二部言教中,了解佛教的義理及哲學意函。一部一部讀下來,原先的意圖已被顛覆,反而在讀經的過程中,與「字」進行深刻的接觸。
當我剛開始讀佛教經典時,最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佛經裡對字的用法與字彙聯成,跳脫了制式的思考模式。剛開始,以世俗解義,煞時如掉在迷宮裡,處處是荊棘;讀了段時間,方才豁然開朗,就像在一個昏天暗地的空間裡,看到一絲曙光。
就以「色」字來說。
心經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什麼是色,甚麼又是空?佛家太強調空,如果真要空掉一切,那麼還須要做人做事嗎?如此,要這世界做什麼呢?初讀經典時的我照字面解釋,陷入表面的陷阱。繼續探究與身入後,方才領會那「色」是代表所有可見的現象界,如人的身體、穿的衣服、桌子、乃至大自然的花草樹木,而非鄙俗的慾念。「空」是不固執於既有的一切,雲且讓它是雲,風且讓它是風。數學觀念所教導的負負得正,在此地正好派上用場。「不」和「異」就是「同」了。色同空,空同色,如此,方可釋懷做為一個人要「堅持」而不「固執」的處事態度。
理想可追尋,幻想卻可喪志。一個「不」與「異」既聯結了現象界與非現象界,同時也顛覆了世俗所謂的世界觀。人外以豈是只有人,天外又何止只有天!佛家其實是有積極的入世性,卻是被誤解的「空」延緩了信仰的腳步。
一個字的用法有萬千,約定俗成的用法在佛經裡卻是另番天地。時日久了,甚至興起意念,當時造字的過程及演變的歷史長河裡,「字」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必迴異於現代的用法。
這個肯定的答案,其實已昭然若揭,只不過在時代推進中,我們遺忘了「字」它所扮演的「傳達」角色,而過於著墨它的外表與內在,急急營營之下,忽視了它根本實在單純的面目。
讀經的日子,是最快樂的時候。許多人世間裡看不慣想不透的事情,往往在佛經的三言兩字中找到突圍的方法。黑暗、鬱沉、結錮的情緒慢慢的找到一個舒放的出口。
念著一個人,想著一件事,久遠以前難忘的景物,常常在自以為放開時,突然在夜間的夢裡以另外一種「彷彿是真實存在」的景象搬演一遍。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弗洛依德以潛意識來解夢。其實佛陀也是解夢個中好手!「心無罣礙,無罣礙故。」心裡沒有所放不下的,夜裡自然能有好眠!多夢者與無夢者的差別也就在這放開的程度大小罷!
一天晚上,讀罷佛經,坐在客廳裡,萬聲俱寂,縷縷沉香迴盪於室。那樣沉靜的空間與時間,是一天當中最舒服的時候。
家事已了。公事也罷。丈夫孩子早已入睡。清清朗朗一個人,完全屬於自己,不用分割給俗務,腦筋特別清明,身體特別輕,能真實面對自己的美好與醜陋。一天中能有這樣的時刻,夫復何求。
我的眼睛瞥到書桌上一個長方形的物體,雖然燈光不夠明亮,我知道那是一方被我久置的硯台。像是「終於等到你」,那方硯台終於耐心地等到了放在我面前的時刻。
洗筆,磨墨,攤開一長落宣紙,經本置於經架,當一切準備妥當,就一盞小燈光暈,我抄起了愣嚴經。
毛筆點刷過宣紙,沙沙聲響在近於無聲的晚上,像翻過浪頭的大水,來勢澎湃。勾撇之間,感受到紙的纖維因水分的滋潤而舒張,因筆的摁壓而有生命。在紙、筆墨與字三者之間所產生的彼此相依關係,如如實實是一個人生的開展。
落筆的手顫抖,恐寫錯了字,又怕歪歪斜斜不成直行,壞了整體的美觀。墨深墨淺,字大字小,懸念的心拉長時間的距離,一個字揹著千萬斤重的期待,寫得不好是必然的。
放下筆,從頭看起。
剎那間懂得如何調適自己的心。把牽掛交給未來。就專心寫。只為寫而寫吧!
再次落筆,順暢多了。
阿難遇劫,佛陀應供完,匆匆趕回,囑咐文殊菩薩快去救阿難!句句抄下來,就像阿難問起的心在何處,一結打過一結,一結解過一結。佛陀陪著我,阿難陪著我,度過無無數個夜晚。
也是抄經的夜晚,不知何時,眼前的百葉窗外透來銀光。
我起身走到窗前。綿綿細細的白雪自高高的天上緩緩滑翔而下。屋頂、枯枝、地面,附著銀白薄膜,在滿黑的天地間,尤為明淨。我的心頓時充盈。那種晶瑩無瑕的美,豈是從人間來!
我打開門,一陣冷風灌身而入。我提起衣領,將人裹在厚衣內。眼前白茫茫一片,真美!宇宙間應該有某種無上的精神在對地球進行修護,所以才有四季,才有讓人驚美的深夜白雪,讓人在無盡的世間壓力、困頓、挫折、無奈與嘆息中,因為心靈些許憾動,才能感受到遙遙天際外,有生命元素在傾聽我們的心聲!
我輕輕閤上眼睛,雙手合十,感念十方諸佛的照護,接納我的不足。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