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曾經對我微笑;好幾次,當我踩著孤單的腳步走在妳的邊緣,海洋好幾次攜著陽光對我溫柔的微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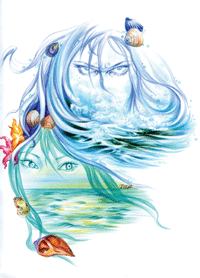
我沒帶禮物,心裡也沒懷藏任何一只空籃子;靠近妳,並不為了偶遇另一張孤獨的表情,也不為了拾撿浮在灘上的其他機會。對妳,我沒有意圖,甚至不帶一點祈求的心。靠近只是因為妳的身邊空曠,空曠到無需任何語言和表情、空曠到允許想念和寂寞的心踽踽獨行。
空曠到可以立即切換── 不必一直看著自己。
就看見妳的表情了。原本平靜的海面,如妳慣常沒有心情的臉孔;忽然間點開了,漾開了或是綻開了。不是吐露、不是攢起,是泛泛牽引起一道原本並不存在的弧線,像天際偶現的一道虹彩;是一條魚,披著煥亮的水漬和天光,從大片的茫然裡落點了一抹顏色,虛無當中,有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動靜。
啊,是妳的表情;是妳看見我的心底。
所有時間只是剎那,漣漪就盪開了;泛泛漫漫向外擴張。當然這不是撫慰、不是給予;孤單的囊袋即便是裝填了所有的海水,不一定就能填得滿。好幾次看見妳的微笑,終於明白,那只是表情,是妳千變萬化的表情中偶爾綻漾的絲縷微笑。
看見好幾次後,覺得妳的微笑含著微微的譏訕之意。
這些表情都點在妳的右眼下方、嘴角上面一點,不是深盪的笑紋,不是由心而起的歡喜,一點都不足以牽連妳整面廣浩的臉頰,僅僅微微如風偶然掀起的小波小漾。
彷彿看見妳的眼神,不是靠過來的凝視或關懷,而是斜看一眼有了點笑意就要偏過頭離開的那種。
這笑容沒有溫度,甚至幾分冷漠。
但是這漣漪就這麼波盪到我的心海裡了。不是嗎,為何孤單?又為何強作孤單?那小小的一方淺池子裡哪來的容量容納孤單。
一愣、一轉,她的微笑一點一點連接成為我心裡的驚嘆,漣漪遂轉化成波濤淹過我的心頭。
許多年了,我深深記得那許多次的片刻,看見了妳回眸之際的微笑。
後來看見妳幾次歡喜,那是由心的開懷。
靠近妳,漸漸不帶任何情緒;就像灘上妳擺弄的滾滾石礫,來來去去在妳的指掌間篩盪,深沉的韻律和節奏,只發出一個單音。這單音其實是千音、萬響所組合成的;那是濤和掏,是衝擊也是掏取。更靠近妳以後,一不留意便聽不見了。
來來去去間,有一次,妳便潑了一灘魚在我的腳前。幾百條有吧,每一條都是晶瑩的珍珠、每一條都是音符;一曲沉穩的單音裡,一群花俏高亢的蹬音;我看出了每一條都是妳胸懷裡的歡喜。
也是短短的瞬間而已;下一波浪潮,妳便悉數收回。
記得,當時我抬起頭對妳微笑;好久不曾從心底盪起的微笑。
發現妳的起伏很大,潮汐只是妳的基本手法。
一波漲退之間,妳會停留;留在最高潮,或停在最低點。
這時,我發現妳驚人的平靜。
那不是因為滿足而平靜,也不是因為低落而放縱;那種平靜是放空一切、放下一切,像一個不再轉動沒有意念的黑洞:沒有生之息,也沒有死之氣,沒有光影、沒有聲音、沒有形體 ... 感覺一扇茫茫薄薄的門扉輕輕閤上。
我看不見妳,最多只能感覺,透過我的想像來感覺妳的平靜、透過我的記憶來模擬一場徹底的休憩。不是疲憊,也不是睡眠,我看見了渾厚、渾圓的水面,陰陰的溶著天空的雲朵,有一點滲漏的光絲,照著水面輕凝的煙靄。妳不再是無垠的廣浩,妳的表情濃縮成一個似有似無的點。
於是聽懂了女高音反覆吟唱著的?酖?酖如海的平靜。
那天黃昏,妳從我的身邊退落到遠遠的天際。
退走時,從空中攀抓了些將要離去的餘光和陰霾,妳轉過頭去,不曉得是否不願意我靠近妳眼裡的淚水,或者不願意我看見妳悲苦的表情。
「怎麼了?」我的探問妳不願意回答。
原本妳懷抱裡的黑色礁石;如此猙獰、如此頑固;裸露了一段在我的眼前,那是觸不得也無法修葺的疼痛。天將要暗了,這道門又厚又重,緊緊的閉鎖在妳和我之間。我只能遠遠的陪著妳,淒愀的等到妳願意回心轉意。
知道妳並不畏懼黑暗,妳曾經與溫柔的月兒終夜攀談,也曾經鋪開胸懷讓星子溶在妳的心池裡洇泳;黑暗是妳的體質,冰冷是妳尋常的體溫,合起來的悲苦,世間將沒有任何一盞火光能夠稍稍照明妳的表情或融解妳的心意。就像沉沒在最深邃的海溝裡,沒有一座山頭能夠露頂。
我的等待含著懷念,妳曾經的透明和澄淨。
我耐心的等待,不一定換得妳善意的回應。
關著的門終於開啟了,妳換了另一個表情面對我。過去的冷漠相較之下還算溫柔。妳搪臂一揮召來了由妳的氣聚合的風、由妳的淚盤成的雨;疾風和暴雨;深深皺凝起妳那可以隨心光滑年輕、可以轉眼蒼老褶皺的臉孔,這時,妳臉上的每脈紋絡全是不受規範的山聳和直墜到底的谷壑。
湧動,不住的洶湧。妳的魚,不安的紛紛深藏;妳的黑色礁石撞擊妳的憤恨,替妳的口,不間斷的吟吼;風抓著妳蒼白的髮絲亂擾著妳的臉;妳的指掌露出獠骨,使勁的拈揉著石礫;妳的臉一片青綠,蒼蒼斑白。
妳開門瞪著我,但我看不見妳的眼。
想像妳的眼神:晚霞夕沒的炭紅,或者,熱烈燃燒的血紅。明白這是妳一時的心情,不是妳願意看我的表情。
妳也曾挑釁的告訴我:「來吧,面對我。」
我沒有離開,腦子裡浮起的始終是妳帶著陽光的溫柔表情。